◎李学军
早饭,很简单,手擀面,卤子汤。我做手擀面,他做卤子汤,几十年如一日,这是我俩生活的常态。
手擀面也不是纯白面的,一大半白面,还掺杂了少许豆面和荞麦面。卤子汤最常做的是:萝卜丝卤子汤,或者西红柿汤。年龄大了,吃得越来越清淡,这样的早餐,有利健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杂粮面占据了我家的主食。蒸馒头掺的杂粮更多,玉米面、荞麦面占据一大半,白面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在物质丰盈的年代,大鱼大肉渐渐淡出我们的餐桌,青菜成了“主角”。这样的生活方式似乎越来越受人们青睐,原因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先生是易胖体质,天天减肥,然而越减越肥。想做到真正减肥,必须先从饮食抓起。
粗粮馒头,清淡小菜,这越来越像我们小时候的生活。
他边切萝卜丝边说:“小时候上学,经过学校食堂,我们村的邻居在食堂做饭,经常给老师们用萝卜丝炒锅下面条,那炒锅的香味飘出来,馋得我直流口水。因为是邻居,有时候还能给我碗汤喝。那种味道,已经深入骨髓了,这辈子都忘不了。”是啊,如果不是深入骨髓,他不会触景生情,又想起那段“美好”的记忆!
我们的童年都有抹不去的记忆,或伤痛,或喜悦,或悲情……记忆的闸门打开,那些久远而琐碎的画面清晰可见。儿时的味道,很熟悉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扑面而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母亲站在灶前忙碌的身影。灶台上放着一个泥土烧制的大瓦盆,从盆的底部到盆沿,有一条长长的裂缝,裂缝左右整齐地排列着一排钉子,乍一看像一条爬行的蜈蚣。母亲说是一位姓齐的手艺人给补的面盆,现在想想那还真是个技术活。面盆里装满了一大盆和好的玉米面,母亲熟练地蒸着窝窝头,那形象,就像一位陶瓷制作者,在精心制作她的工艺作品。这作品,就是全家人的午饭。渐渐地,母亲的身影换成姐姐,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午餐,伴随我整个童年。
和窝窝头搭档最多的是咸菜。秋季收获的萝卜,母亲会腌一大缸,供全家人吃一年。就这样年复一年,从没断过。就是这样的咸菜,母亲还控制我们食用。至今记得那口一号大缸,上面盖着一口有破洞的大锅,下雨天还要在上面盖一层塑料布,防止进雨水,坏了那半缸卤水。
窝头、咸菜,占据了我童年的主要味蕾。
最难忘的是母亲每次蒸饭都会为父亲蒸上少量的白面馒头。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生活再难,母亲也不会亏待父亲。每当身体不舒服,母亲也会给我白面馒头,每次我都含在嘴里不舍得咽下去,那味道,唇齿留香。有时我甚至盼着生病,只为能吃上那口白面馒头。
童年的白面馒头,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家里改善伙食,母亲会炖上半锅白菜或者萝卜,放几片猪肉炼炼油,一人一大碗,吃完了再盛一碗,不管母亲炖多少,都吃得连菜汤也不剩。懂事的姐姐总是偷偷留出一碗,留给父亲下顿吃。姐姐碗里的肉片不是给父亲,就是给哥哥或者妹妹。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很温暖。
有时候母亲还会用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馅,放上少许肉沫,包菜包子。包子皮照样是地瓜面为主,加上少许白面。一锅热气腾腾的包子,一眨眼就去了一半,我们兄妹围着锅台吃得津津有味。
逢年过节,我们才吃上一顿饺子。母亲先包好年夜饭的白面饺子,再包杂粮面的饺子,通常都是掺上地瓜面,那黑乎乎的杂粮面饺子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味佳肴。
记得姐姐腊月二十九下午就开始准备饺子馅,年三十上午开始包饺子,一包一整天。一口六印大锅煮上半锅,一顿吃完。想想那些饺子,现在一天都吃不完。那个时候屋子小,母亲通常把我们这些不干活的撵到炕上去,免得碍事,只留下姐姐和自己忙年。姐姐烧火,母亲煮饺子,我和妹妹趴在炕沿上,就像等待喂食的小燕子,两眼盯着锅里翻滚的饺子,口水不住地往下咽。
儿时的饺子,吃出了浓浓的年味!
渐渐地,玉米窝窝头换成杂粮馒头,又换成白面馒头;缸里的咸菜不见了,冰箱里装满了新鲜蔬菜和海鲜;母亲的六印大锅,换成了电饭锅和小巧的炒锅……生活越来越富足,饭菜越来越丰盛。
富足的我们开始重视饮食健康,低盐低油低糖,养生成为热门话题。曾经发誓这辈子都不想吃的玉米、地瓜、萝卜,成了“养生佳品”。儿时的饭菜再度盛行,重新被人们重视,端上饭桌。同样的饭菜,却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早饭,很简单,手擀面,卤子汤。我做手擀面,他做卤子汤,几十年如一日,这是我俩生活的常态。
手擀面也不是纯白面的,一大半白面,还掺杂了少许豆面和荞麦面。卤子汤最常做的是:萝卜丝卤子汤,或者西红柿汤。年龄大了,吃得越来越清淡,这样的早餐,有利健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杂粮面占据了我家的主食。蒸馒头掺的杂粮更多,玉米面、荞麦面占据一大半,白面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在物质丰盈的年代,大鱼大肉渐渐淡出我们的餐桌,青菜成了“主角”。这样的生活方式似乎越来越受人们青睐,原因是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先生是易胖体质,天天减肥,然而越减越肥。想做到真正减肥,必须先从饮食抓起。
粗粮馒头,清淡小菜,这越来越像我们小时候的生活。
他边切萝卜丝边说:“小时候上学,经过学校食堂,我们村的邻居在食堂做饭,经常给老师们用萝卜丝炒锅下面条,那炒锅的香味飘出来,馋得我直流口水。因为是邻居,有时候还能给我碗汤喝。那种味道,已经深入骨髓了,这辈子都忘不了。”是啊,如果不是深入骨髓,他不会触景生情,又想起那段“美好”的记忆!
我们的童年都有抹不去的记忆,或伤痛,或喜悦,或悲情……记忆的闸门打开,那些久远而琐碎的画面清晰可见。儿时的味道,很熟悉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扑面而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母亲站在灶前忙碌的身影。灶台上放着一个泥土烧制的大瓦盆,从盆的底部到盆沿,有一条长长的裂缝,裂缝左右整齐地排列着一排钉子,乍一看像一条爬行的蜈蚣。母亲说是一位姓齐的手艺人给补的面盆,现在想想那还真是个技术活。面盆里装满了一大盆和好的玉米面,母亲熟练地蒸着窝窝头,那形象,就像一位陶瓷制作者,在精心制作她的工艺作品。这作品,就是全家人的午饭。渐渐地,母亲的身影换成姐姐,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午餐,伴随我整个童年。
和窝窝头搭档最多的是咸菜。秋季收获的萝卜,母亲会腌一大缸,供全家人吃一年。就这样年复一年,从没断过。就是这样的咸菜,母亲还控制我们食用。至今记得那口一号大缸,上面盖着一口有破洞的大锅,下雨天还要在上面盖一层塑料布,防止进雨水,坏了那半缸卤水。
窝头、咸菜,占据了我童年的主要味蕾。
最难忘的是母亲每次蒸饭都会为父亲蒸上少量的白面馒头。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生活再难,母亲也不会亏待父亲。每当身体不舒服,母亲也会给我白面馒头,每次我都含在嘴里不舍得咽下去,那味道,唇齿留香。有时我甚至盼着生病,只为能吃上那口白面馒头。
童年的白面馒头,至今让我念念不忘。
家里改善伙食,母亲会炖上半锅白菜或者萝卜,放几片猪肉炼炼油,一人一大碗,吃完了再盛一碗,不管母亲炖多少,都吃得连菜汤也不剩。懂事的姐姐总是偷偷留出一碗,留给父亲下顿吃。姐姐碗里的肉片不是给父亲,就是给哥哥或者妹妹。那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很温暖。
有时候母亲还会用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馅,放上少许肉沫,包菜包子。包子皮照样是地瓜面为主,加上少许白面。一锅热气腾腾的包子,一眨眼就去了一半,我们兄妹围着锅台吃得津津有味。
逢年过节,我们才吃上一顿饺子。母亲先包好年夜饭的白面饺子,再包杂粮面的饺子,通常都是掺上地瓜面,那黑乎乎的杂粮面饺子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美味佳肴。
记得姐姐腊月二十九下午就开始准备饺子馅,年三十上午开始包饺子,一包一整天。一口六印大锅煮上半锅,一顿吃完。想想那些饺子,现在一天都吃不完。那个时候屋子小,母亲通常把我们这些不干活的撵到炕上去,免得碍事,只留下姐姐和自己忙年。姐姐烧火,母亲煮饺子,我和妹妹趴在炕沿上,就像等待喂食的小燕子,两眼盯着锅里翻滚的饺子,口水不住地往下咽。
儿时的饺子,吃出了浓浓的年味!
渐渐地,玉米窝窝头换成杂粮馒头,又换成白面馒头;缸里的咸菜不见了,冰箱里装满了新鲜蔬菜和海鲜;母亲的六印大锅,换成了电饭锅和小巧的炒锅……生活越来越富足,饭菜越来越丰盛。
富足的我们开始重视饮食健康,低盐低油低糖,养生成为热门话题。曾经发誓这辈子都不想吃的玉米、地瓜、萝卜,成了“养生佳品”。儿时的饭菜再度盛行,重新被人们重视,端上饭桌。同样的饭菜,却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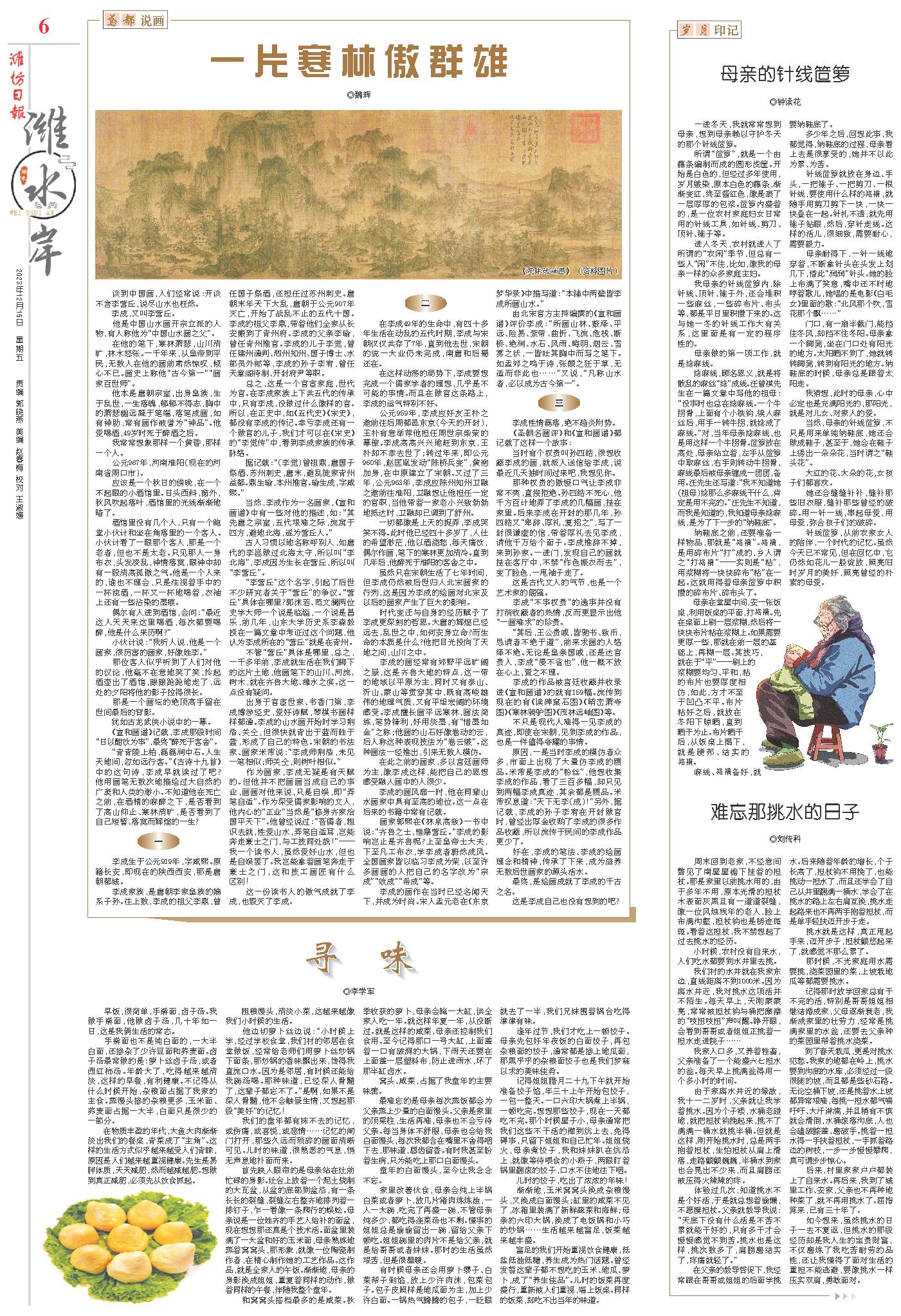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7/Page07-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215/08/Page08-15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