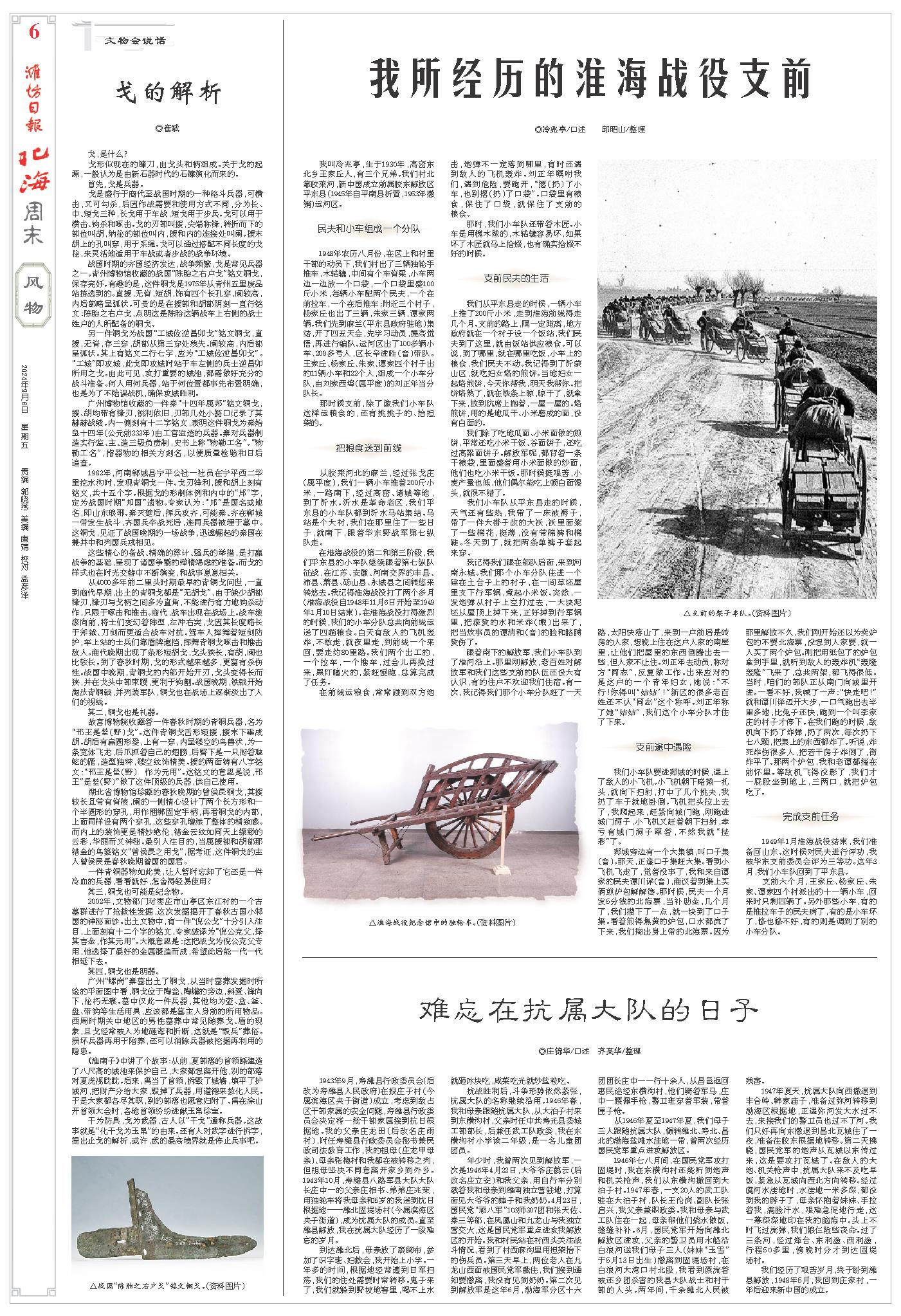◎庄锦华/口述 齐英华/整理
1943年9月,寿潍县行政委员会(后改为寿潍县人民政府)在报庄子村(今属滨海区央子街道)成立,考虑到敌占区干部家属的安全问题,寿潍县行政委员会决定将一批干部家属接到抗日根据地。我的父亲庄龙田(后改名庄雨村),时任寿潍县行政委员会秘书兼民政司法教育工作,我的祖母(庄龙甲母亲)、母亲张梅村和我都在被转移之列,但祖母坚决不同意离开家乡到外乡。1943年10月,寿潍县八路军县大队大队长庄中一的父亲庄相书、弟弟庄兆荣,用独轮车将我母亲和5岁的我送到抗日根据地——潍北固堤场村(今属滨海区央子街道),成为抗属大队的成员。直至潍县解放,我在抗属大队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到达潍北后,母亲放了裹脚布,参加了识字班、妇救会,我开始上小学。一年多的时间,根据地经常遭到日军扫荡,我们的住处需要时常转移。鬼子来了,我们就躲到野坡地窖里,喝不上水就砸冰块吃,咸菜吃光就炒盐粒吃。
抗战胜利后,斗争形势依然紧张,抗属大队的名称继续沿用。1946年春,我和母亲跟随抗属大队,从大泊子村来到东横沟村,父亲时任中共寿光县委城工部部长,后兼任武工队政委,我在东横沟村小学读二年级,是一名儿童团团员。
年少时,我曾两次见到解放军,一次是1946年4月22日,大爷爷庄鹤云(后改名庄立安)和我父亲,用自行车分别载着我和母亲到潍南独立营驻地,打算面见大爷爷的婶子和我奶奶。4月23日,国民党“顽八军”103师307团和张天佐、秦三等部,在凤凰山和九龙山与我独立营交火,这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我解放区的开始。我和村民站在村西头关注战斗情况,看到了村西麻沟里用担架抬下的伤兵员。第三天早上,两位老人在九龙山西面被国民党军截住,我们接到通知要撤离,我没有见到奶奶。第二次见到解放军是这年6月,渤海军分区十六团团长庄中一一行十余人,从昌邑返回惠民途经东横沟村,他们骑着军马,庄中一腰佩手枪,警卫班穿着军装,带着匣子枪。
从1946年夏至1947年夏,我们母子三人跟随抗属大队,辗转潍北、寿北、昌北的渤海盐滩水洼地一带,曾两次经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解放区。
1946年七八月间,在国民党军攻打固堤时,我在东横沟村还能听到炮声和机关枪声,我们从东横沟撤回到大泊子村。1947年春,一支20人的武工队驻在大泊子村,队长王伦岗、副队长张启兴,我父亲兼职政委。我和母亲与武工队住在一起,母亲帮他们烧水做饭,缝缝补补。6月,国民党军开始向潍北解放区进攻,父亲的警卫员用木船沿白浪河送我们母子三人(妹妹“玉雪”于5月13日出生)撤离到固堤场村,在白浪河大湾口村北段,我看到漂流着被还乡团杀害的我县大队战士和村干部的人头。两年间,千余潍北人民被残害。
1947年夏天,抗属大队向西撤退到丰台岭、韩家庙子,准备过弥河转移到渤海区根据地,正遇弥河发大水过不去,来接我们的警卫员也过不了河。我们只好再向东撤退到昌北瓦城住了一夜,准备往胶东根据地转移。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的炮声从瓦城以东传过来,这是要攻打瓦城了。在敌人的大炮、机关枪声中,抗属大队来不及吃早饭,紧急从瓦城向西北方向转移。经过虞河水洼地时,水洼地一米多深,都没到我的脖子了,母亲怀抱着妹妹、手拉着我,满脸汗水,艰难急促地行走,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头上不时飞过流弹,我们娘仨险些丧命。过了三条河,经过烽台、东利渔、西利渔,行程50多里,傍晚时分才到达固堤场村。
我们经历了艰苦岁月,终于盼到潍县解放,1948年5月,我回到庄家村,一年后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1943年9月,寿潍县行政委员会(后改为寿潍县人民政府)在报庄子村(今属滨海区央子街道)成立,考虑到敌占区干部家属的安全问题,寿潍县行政委员会决定将一批干部家属接到抗日根据地。我的父亲庄龙田(后改名庄雨村),时任寿潍县行政委员会秘书兼民政司法教育工作,我的祖母(庄龙甲母亲)、母亲张梅村和我都在被转移之列,但祖母坚决不同意离开家乡到外乡。1943年10月,寿潍县八路军县大队大队长庄中一的父亲庄相书、弟弟庄兆荣,用独轮车将我母亲和5岁的我送到抗日根据地——潍北固堤场村(今属滨海区央子街道),成为抗属大队的成员。直至潍县解放,我在抗属大队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到达潍北后,母亲放了裹脚布,参加了识字班、妇救会,我开始上小学。一年多的时间,根据地经常遭到日军扫荡,我们的住处需要时常转移。鬼子来了,我们就躲到野坡地窖里,喝不上水就砸冰块吃,咸菜吃光就炒盐粒吃。
抗战胜利后,斗争形势依然紧张,抗属大队的名称继续沿用。1946年春,我和母亲跟随抗属大队,从大泊子村来到东横沟村,父亲时任中共寿光县委城工部部长,后兼任武工队政委,我在东横沟村小学读二年级,是一名儿童团团员。
年少时,我曾两次见到解放军,一次是1946年4月22日,大爷爷庄鹤云(后改名庄立安)和我父亲,用自行车分别载着我和母亲到潍南独立营驻地,打算面见大爷爷的婶子和我奶奶。4月23日,国民党“顽八军”103师307团和张天佐、秦三等部,在凤凰山和九龙山与我独立营交火,这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我解放区的开始。我和村民站在村西头关注战斗情况,看到了村西麻沟里用担架抬下的伤兵员。第三天早上,两位老人在九龙山西面被国民党军截住,我们接到通知要撤离,我没有见到奶奶。第二次见到解放军是这年6月,渤海军分区十六团团长庄中一一行十余人,从昌邑返回惠民途经东横沟村,他们骑着军马,庄中一腰佩手枪,警卫班穿着军装,带着匣子枪。
从1946年夏至1947年夏,我们母子三人跟随抗属大队,辗转潍北、寿北、昌北的渤海盐滩水洼地一带,曾两次经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解放区。
1946年七八月间,在国民党军攻打固堤时,我在东横沟村还能听到炮声和机关枪声,我们从东横沟撤回到大泊子村。1947年春,一支20人的武工队驻在大泊子村,队长王伦岗、副队长张启兴,我父亲兼职政委。我和母亲与武工队住在一起,母亲帮他们烧水做饭,缝缝补补。6月,国民党军开始向潍北解放区进攻,父亲的警卫员用木船沿白浪河送我们母子三人(妹妹“玉雪”于5月13日出生)撤离到固堤场村,在白浪河大湾口村北段,我看到漂流着被还乡团杀害的我县大队战士和村干部的人头。两年间,千余潍北人民被残害。
1947年夏天,抗属大队向西撤退到丰台岭、韩家庙子,准备过弥河转移到渤海区根据地,正遇弥河发大水过不去,来接我们的警卫员也过不了河。我们只好再向东撤退到昌北瓦城住了一夜,准备往胶东根据地转移。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的炮声从瓦城以东传过来,这是要攻打瓦城了。在敌人的大炮、机关枪声中,抗属大队来不及吃早饭,紧急从瓦城向西北方向转移。经过虞河水洼地时,水洼地一米多深,都没到我的脖子了,母亲怀抱着妹妹、手拉着我,满脸汗水,艰难急促地行走,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头上不时飞过流弹,我们娘仨险些丧命。过了三条河,经过烽台、东利渔、西利渔,行程50多里,傍晚时分才到达固堤场村。
我们经历了艰苦岁月,终于盼到潍县解放,1948年5月,我回到庄家村,一年后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7/Page07-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40906/08/Page08-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