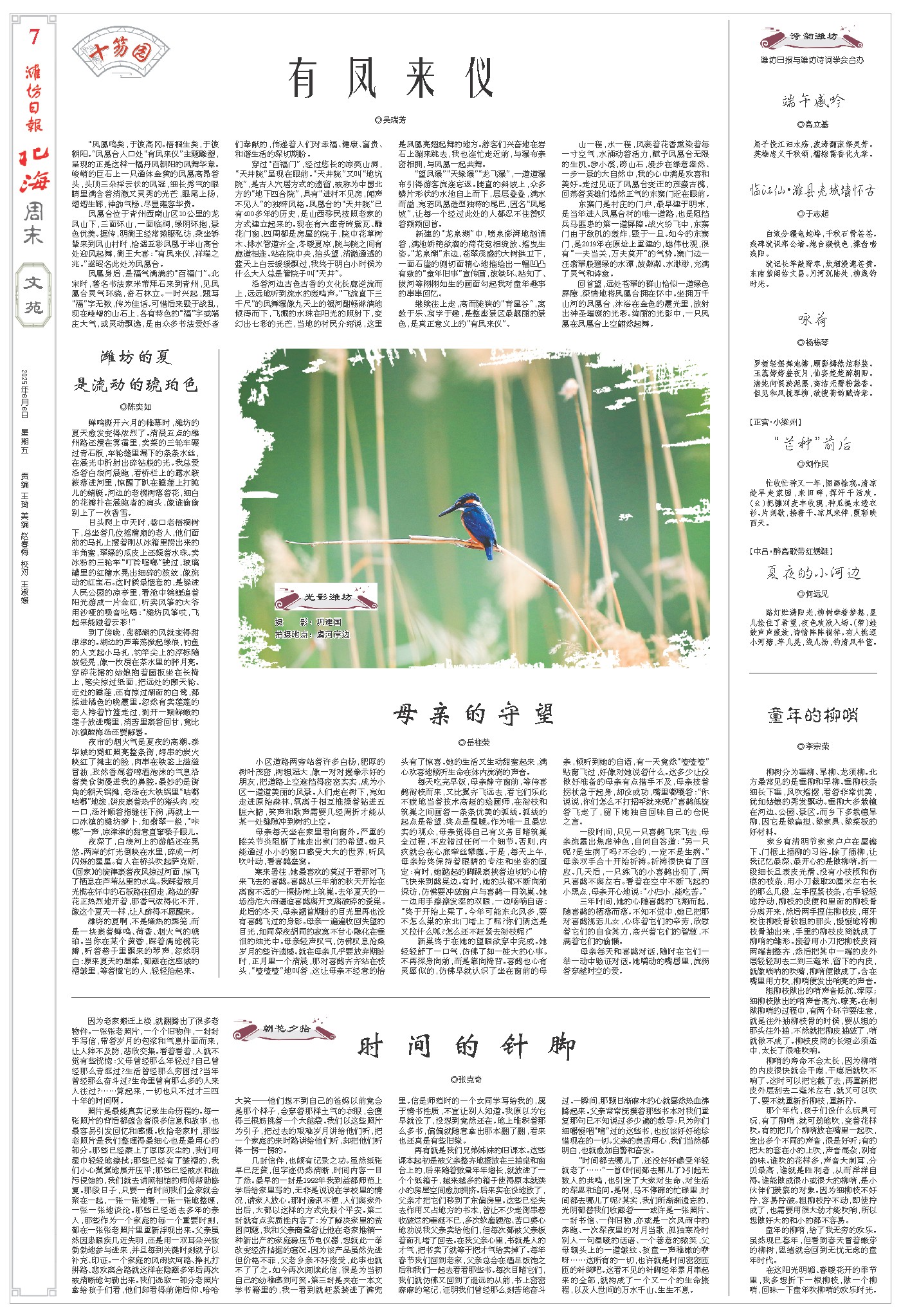05版:北海周末
05版:北海周末
- * 潍坊历史名人
- * 一座城·两代人·三展馆
- *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
 08版:北海周末·悦览
08版:北海周末·悦览
- *
致敬永恒的
家国情怀 - * 世代传承的力量
- * 光与影赋予生命以意义
- * 全民阅读 一起读书
- * 剧 院 之 声
◎张克奇
因为老家搬迁上楼,就翻腾出了很多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旧物件,一封封手写信,带着岁月的包浆和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猝不及防,悲欣交集。看着看着,人就不觉有些恍惚:父母曾经那么年轻过?自己曾经那么青涩过?生活曾经那么穷困过?当年曾经那么奋斗过?生命里曾有那么多的人来人往过?……算起来,一切也只不过才三四十年的时间啊。
照片是最能真实记录生命历程的。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蕴含着很多信息和故事,也最容易引发回忆和感慨。收拾老家时,那些老照片是我们整理得最细心也是最用心的部分。那些已经蒙上了厚厚灰尘的,我们用湿巾轻轻地擦拭;那些已经有了皱褶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展开压平;那些已经被水和油污侵蚀的,我们就去请照相馆的师傅帮助修复。那段日子,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全家就会聚在一起,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整理,一张一张地谈论。那些已经逝去多年的亲人,那些作为一个家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在一张张老照片里重新浮现出来。父亲虽然因患眼疾几近失明,还是用一双耳朵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并且每到关键时刻就予以补充、印证。一个家庭的风雨坎坷路、挣扎打拼路、悲欢离合路就这样在隐藏多年后再次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我们选取一部分老照片拿给孩子们看,他们却看得前俯后仰、哈哈大笑——他们想不到自己的爸妈以前竟会是那个样子,会穿着那样土气的衣服,会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大脑袋。我们以这些照片为引子,把过去的艰难岁月讲给他们听,把一个家庭的来时路讲给他们听,却把他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几封信件,也颇有记录之功。虽然纸张早已泛黄,但字迹仍然清晰,时间内容一目了然。最早的一封是1992年我到益都师范上学后给家里写的,无非是说说在学校里的情况,请家人放心。那时通讯不便,人们离家外出后,大都以这样的方式先报个平安。第二封就有点实质性内容了:为了解决家里的贫困问题,我和父亲商量着让他在老家推销一种新出产的家庭稳压节电仪器,想就此一举改变经济拮据的窘况。因为该产品虽然先进但价格不菲,父老乡亲不好接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如今再次阅读此信,很是为当初自己的幼稚感到可笑。第三封是夹在一本文学书籍里的,我一看到就赶紧装进了裤兜里。信是师范时的一个女同学写给我的,属于情书性质,不宜让别人知道。我原以为它早就没了,没想到竟然还在。地上堆积着那么多书,偏偏就随意拿出那本翻了翻,看来也还真是有些旧缘。
再有就是我们兄弟姊妹的旧课本。这些课本起初是被父亲整齐地摆放在三抽桌和窗台上的,后来随着数量年年增长,就放进了一个个纸箱子,越来越多的箱子使得原本就狭小的房屋空间愈加拥挤。后来实在没地放了,父亲才把它们移到了东偏房里。这些已经失去作用又占地方的书本,曾让不少走街串巷收破烂的垂涎不已,多次软磨硬泡、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父亲卖给他们,但每次都被父亲板着面孔堵了回去。在我父亲心里,书就是人的才气,把书卖了就等于把才气给卖掉了。每年春节我们回到老家,父亲总会在酒足饭饱之后和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书。每次目睹它们,我们就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从前,书上密密麻麻的笔记,证明我们曾经那么刻苦地奋斗过。一瞬间,那颗日渐麻木的心就蓦然热血沸腾起来。父亲常常抚摸着那些书本对我们重复那句已不知说过多少遍的教导:只为你们细嚼慢咽“啃”过的这些书,也应该好好地珍惜现在的一切。父亲的良苦用心,我们当然都明白,也就愈加自警和奋发。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也引发了大家对生命、对生活的深思和追问。是啊,马不停蹄的忙碌里,时间都去哪儿了呢?其实,我们所渐渐遗忘的,光阴都替我们收藏着——或许是一张照片、一封书信、一件旧物,亦或是一次风雨中的奔跑、一次深夜里的对月当歌,孤独寒冷时别人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善意的微笑,父母额头上的一道皱纹、孩童一声稚嫩的咿呀……这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时间密密匝匝的针脚吧。这看不见的针脚经年累月串起来的全部,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旅程,以及人世间的万水千山、生生不息。
因为老家搬迁上楼,就翻腾出了很多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旧物件,一封封手写信,带着岁月的包浆和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猝不及防,悲欣交集。看着看着,人就不觉有些恍惚:父母曾经那么年轻过?自己曾经那么青涩过?生活曾经那么穷困过?当年曾经那么奋斗过?生命里曾有那么多的人来人往过?……算起来,一切也只不过才三四十年的时间啊。
照片是最能真实记录生命历程的。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蕴含着很多信息和故事,也最容易引发回忆和感慨。收拾老家时,那些老照片是我们整理得最细心也是最用心的部分。那些已经蒙上了厚厚灰尘的,我们用湿巾轻轻地擦拭;那些已经有了皱褶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展开压平;那些已经被水和油污侵蚀的,我们就去请照相馆的师傅帮助修复。那段日子,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全家就会聚在一起,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整理,一张一张地谈论。那些已经逝去多年的亲人,那些作为一个家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在一张张老照片里重新浮现出来。父亲虽然因患眼疾几近失明,还是用一双耳朵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并且每到关键时刻就予以补充、印证。一个家庭的风雨坎坷路、挣扎打拼路、悲欢离合路就这样在隐藏多年后再次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我们选取一部分老照片拿给孩子们看,他们却看得前俯后仰、哈哈大笑——他们想不到自己的爸妈以前竟会是那个样子,会穿着那样土气的衣服,会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大脑袋。我们以这些照片为引子,把过去的艰难岁月讲给他们听,把一个家庭的来时路讲给他们听,却把他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几封信件,也颇有记录之功。虽然纸张早已泛黄,但字迹仍然清晰,时间内容一目了然。最早的一封是1992年我到益都师范上学后给家里写的,无非是说说在学校里的情况,请家人放心。那时通讯不便,人们离家外出后,大都以这样的方式先报个平安。第二封就有点实质性内容了:为了解决家里的贫困问题,我和父亲商量着让他在老家推销一种新出产的家庭稳压节电仪器,想就此一举改变经济拮据的窘况。因为该产品虽然先进但价格不菲,父老乡亲不好接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如今再次阅读此信,很是为当初自己的幼稚感到可笑。第三封是夹在一本文学书籍里的,我一看到就赶紧装进了裤兜里。信是师范时的一个女同学写给我的,属于情书性质,不宜让别人知道。我原以为它早就没了,没想到竟然还在。地上堆积着那么多书,偏偏就随意拿出那本翻了翻,看来也还真是有些旧缘。
再有就是我们兄弟姊妹的旧课本。这些课本起初是被父亲整齐地摆放在三抽桌和窗台上的,后来随着数量年年增长,就放进了一个个纸箱子,越来越多的箱子使得原本就狭小的房屋空间愈加拥挤。后来实在没地放了,父亲才把它们移到了东偏房里。这些已经失去作用又占地方的书本,曾让不少走街串巷收破烂的垂涎不已,多次软磨硬泡、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父亲卖给他们,但每次都被父亲板着面孔堵了回去。在我父亲心里,书就是人的才气,把书卖了就等于把才气给卖掉了。每年春节我们回到老家,父亲总会在酒足饭饱之后和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书。每次目睹它们,我们就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从前,书上密密麻麻的笔记,证明我们曾经那么刻苦地奋斗过。一瞬间,那颗日渐麻木的心就蓦然热血沸腾起来。父亲常常抚摸着那些书本对我们重复那句已不知说过多少遍的教导:只为你们细嚼慢咽“啃”过的这些书,也应该好好地珍惜现在的一切。父亲的良苦用心,我们当然都明白,也就愈加自警和奋发。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也引发了大家对生命、对生活的深思和追问。是啊,马不停蹄的忙碌里,时间都去哪儿了呢?其实,我们所渐渐遗忘的,光阴都替我们收藏着——或许是一张照片、一封书信、一件旧物,亦或是一次风雨中的奔跑、一次深夜里的对月当歌,孤独寒冷时别人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善意的微笑,父母额头上的一道皱纹、孩童一声稚嫩的咿呀……这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时间密密匝匝的针脚吧。这看不见的针脚经年累月串起来的全部,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旅程,以及人世间的万水千山、生生不息。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606/08/Page08-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