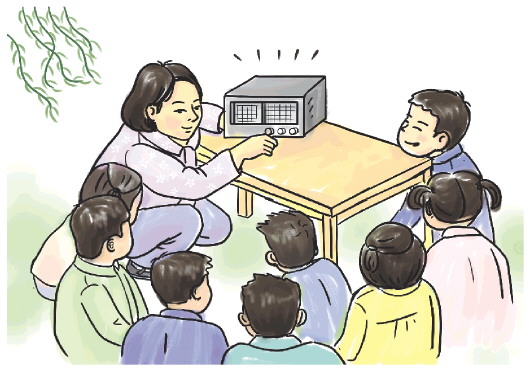06版:潍水岸
06版:潍水岸
- * 一柱擎天寨子崮
- * 听广播
- * 那年,那月,那些米花儿
- * 父亲的芒种
 07版:十笏园
07版:十笏园
- * 岁月之痕
- * 一把呢喃的镰刀
- * 姥姥陪护记
- *
【中吕·山坡羊】
过“六一” - *
【正宫·塞鸿秋】
忆童年 - *
【越调·小桃红】
放学了 - *
【中吕·山坡羊】
童年 - *
【双调·折桂令】
小学生放学后 - *
【双调·水仙子】
忆童年 - * 岁月深处童年亲
- *
童年
跑过一条记忆的巷
 08版:教育
08版:教育
- * 图片新闻
- * 语 文
- * 数 学
- * 化 学
- * 生 物
- * 历 史
- * 物 理
- * 做学生的良师和益友
- *
官庄镇官庄小学
筑牢防溺水防线
保障学生安全 - *
安丘经济开发区小学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 *
高新区浞景学校
推进家庭教育
与思政课协同育人 - * 图片新闻
- * 让评价任务成为学习助推器
听广播,又叫听收音机、听新闻,也叫听戏匣子、听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谁家里有一部收音机,那可是很稀罕的事。
那时学校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让我们列出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看看各家各户都有些什么好东西,比如看谁家有了桌椅板凳、钟表、暖壶、钢笔……而好东西中顶顶重要的大件,当属收音机。
家里的大人都去上班了,姥姥就开始了她一天的忙活。一边收拾家务,一边让我自己在那里玩着,一边打开收音机。姥姥是小脚老太太,没上过学,不识字,印象中她别的不听,只听戏,听京剧、听评剧。
我看着那个能发出各种好听声音的小黑盒子,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以为里边一定是有一些小人儿住着,他们在里边又会唱歌又会演戏,就像戏台子上那些金光闪闪的大将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俊媳妇一样。
后来,在大人们打开收音机后盖保养修理时,我终于发现了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那些直直伫立的复杂的电子管,像极了微缩的人类城市中的摩天大楼,那电子管之间的缝隙和线路就像夹杂在大楼中的街道,遗憾的是在那里没有大城市的车水马龙,也没有唱歌唱戏的小人儿国里的小人儿。
收音机是我幼时的玩伴,在看小人儿书、看小说之前,我先从广播里学到了许多许多。
让我每天都急切地等在收音机前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和《星星火炬》。这两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前后紧挨着的,每天晚饭前,收音机里会传出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哒嘀哒,哒嘀哒,哒嘀嘀哒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伴我度过金色的童年。我还喜欢孙爷爷与一帮小孩子有讲有听、有问有答的互动节目。那时小脑瓜记事快,有一次孙爷爷教了小朋友一个关于钟表的谜语儿歌:“弟弟长,哥哥短,俩人赛跑大家看。弟弟跑了十二圈,哥哥一圈才跑完。”收音机里的小孩跟着孙爷爷反反复复说了好多遍才记住,我听了一遍就能明明白白地记下来了。
后来的几年,我每天最要紧的事,是收听中午12点的曲艺节目、长篇评书连播。那时谁家要是有个收音机,旁边肯定还有个抻长脖子的毛绒绒的小脑袋或者一群挤在一起的毛孩子,端着饭碗攥着半拉窝头或啃着一块热地瓜,聚精会神侧耳聆听,沉迷在袁阔成声情并茂、活灵活现、风趣幽默、出神入化的评书说讲意境之中。我一集不落地听完了《平原枪声》《烈火金钢》《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每天到了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把刚听来的“上回书说到”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表现与同学们兴高采烈地重温一遍,互相欣赏、互相补充、精彩纷呈——马英、王二虎、肖飞、丁尚武、杨子荣、少剑波、白茹、座山雕、许大马棒、小炉匠、蝴蝶迷、魏强、汪霞、哈巴狗、刁世贵、刘奎胜、金环、银环、关敬陶、杨晓东……
有一年,兴起了一阵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自己组装收音机”的活动,市面上有专门科普无线电广播的小册子和图纸,按照说明搞来磁铁,弄来漆包线缠绕线圈,买个耳机或耳塞,用长木杆支起铁丝天线……就差不多能听到嗞嗞拉拉的动静,能听到一两个电台的广播了。当然这都是大孩子才能捣鼓的东西,那些有大哥哥的小伙伴才有福捞着跟着听听。我没有哥哥,兴组装收音机的时候我只能去同桌黄中超家,他趁二哥不在的时候小小心心地让我戴上耳机听了那么一听,耳朵里传来了很远的地方的声音,我觉得很新鲜、很神奇、很吃惊。
后来又有了一种更厉害的东西,和半块砖头一样大的微型收音机,很轻便,可以随身带着,走到哪儿听到哪儿。有了这种“高级货”就是不一样,夏天的夜晚,躺在稿荐(稻草、麦秸等编成的垫子)上乘凉,旁边扇着蒲扇、喝着茶的叔叔就聊起了他提溜着的收音机,什么牌子的?红灯的?凯歌的。
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没有订报的习惯,想读报的大都去街头的阅报栏。广播却无处不在,每个县都有广播站,每个单位都有高音大喇叭,就算连电也没通的农村,也得先安上“大喇叭”。单位也会组织集体收听广播,如果中央台有什么重要广播,大家都会安静下来支楞起耳朵好好听。
那时的广播喇叭,无处不在:楼顶上、屋顶上、树顶上、水塔顶上、电线杆上……除了按时广播的喇叭,我们还在大卡车车头、车尾、两侧安装喇叭,这是单位的宣传车,宣传车开到哪里,大喇叭就响到哪里。每个清晨,从《东方红》的旋律中开始,每个夜晚,在《国际歌》中结束。听新闻、听社论、听天气预报、听电影录音剪辑……无处不在的广播,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
那时学校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让我们列出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看看各家各户都有些什么好东西,比如看谁家有了桌椅板凳、钟表、暖壶、钢笔……而好东西中顶顶重要的大件,当属收音机。
家里的大人都去上班了,姥姥就开始了她一天的忙活。一边收拾家务,一边让我自己在那里玩着,一边打开收音机。姥姥是小脚老太太,没上过学,不识字,印象中她别的不听,只听戏,听京剧、听评剧。
我看着那个能发出各种好听声音的小黑盒子,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以为里边一定是有一些小人儿住着,他们在里边又会唱歌又会演戏,就像戏台子上那些金光闪闪的大将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俊媳妇一样。
后来,在大人们打开收音机后盖保养修理时,我终于发现了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那些直直伫立的复杂的电子管,像极了微缩的人类城市中的摩天大楼,那电子管之间的缝隙和线路就像夹杂在大楼中的街道,遗憾的是在那里没有大城市的车水马龙,也没有唱歌唱戏的小人儿国里的小人儿。
收音机是我幼时的玩伴,在看小人儿书、看小说之前,我先从广播里学到了许多许多。
让我每天都急切地等在收音机前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小喇叭》和《星星火炬》。这两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前后紧挨着的,每天晚饭前,收音机里会传出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哒嘀哒,哒嘀哒,哒嘀嘀哒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伴我度过金色的童年。我还喜欢孙爷爷与一帮小孩子有讲有听、有问有答的互动节目。那时小脑瓜记事快,有一次孙爷爷教了小朋友一个关于钟表的谜语儿歌:“弟弟长,哥哥短,俩人赛跑大家看。弟弟跑了十二圈,哥哥一圈才跑完。”收音机里的小孩跟着孙爷爷反反复复说了好多遍才记住,我听了一遍就能明明白白地记下来了。
后来的几年,我每天最要紧的事,是收听中午12点的曲艺节目、长篇评书连播。那时谁家要是有个收音机,旁边肯定还有个抻长脖子的毛绒绒的小脑袋或者一群挤在一起的毛孩子,端着饭碗攥着半拉窝头或啃着一块热地瓜,聚精会神侧耳聆听,沉迷在袁阔成声情并茂、活灵活现、风趣幽默、出神入化的评书说讲意境之中。我一集不落地听完了《平原枪声》《烈火金钢》《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每天到了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把刚听来的“上回书说到”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表现与同学们兴高采烈地重温一遍,互相欣赏、互相补充、精彩纷呈——马英、王二虎、肖飞、丁尚武、杨子荣、少剑波、白茹、座山雕、许大马棒、小炉匠、蝴蝶迷、魏强、汪霞、哈巴狗、刁世贵、刘奎胜、金环、银环、关敬陶、杨晓东……
有一年,兴起了一阵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自己组装收音机”的活动,市面上有专门科普无线电广播的小册子和图纸,按照说明搞来磁铁,弄来漆包线缠绕线圈,买个耳机或耳塞,用长木杆支起铁丝天线……就差不多能听到嗞嗞拉拉的动静,能听到一两个电台的广播了。当然这都是大孩子才能捣鼓的东西,那些有大哥哥的小伙伴才有福捞着跟着听听。我没有哥哥,兴组装收音机的时候我只能去同桌黄中超家,他趁二哥不在的时候小小心心地让我戴上耳机听了那么一听,耳朵里传来了很远的地方的声音,我觉得很新鲜、很神奇、很吃惊。
后来又有了一种更厉害的东西,和半块砖头一样大的微型收音机,很轻便,可以随身带着,走到哪儿听到哪儿。有了这种“高级货”就是不一样,夏天的夜晚,躺在稿荐(稻草、麦秸等编成的垫子)上乘凉,旁边扇着蒲扇、喝着茶的叔叔就聊起了他提溜着的收音机,什么牌子的?红灯的?凯歌的。
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没有订报的习惯,想读报的大都去街头的阅报栏。广播却无处不在,每个县都有广播站,每个单位都有高音大喇叭,就算连电也没通的农村,也得先安上“大喇叭”。单位也会组织集体收听广播,如果中央台有什么重要广播,大家都会安静下来支楞起耳朵好好听。
那时的广播喇叭,无处不在:楼顶上、屋顶上、树顶上、水塔顶上、电线杆上……除了按时广播的喇叭,我们还在大卡车车头、车尾、两侧安装喇叭,这是单位的宣传车,宣传车开到哪里,大喇叭就响到哪里。每个清晨,从《东方红》的旋律中开始,每个夜晚,在《国际歌》中结束。听新闻、听社论、听天气预报、听电影录音剪辑……无处不在的广播,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7/Page07-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02/08/Page08-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