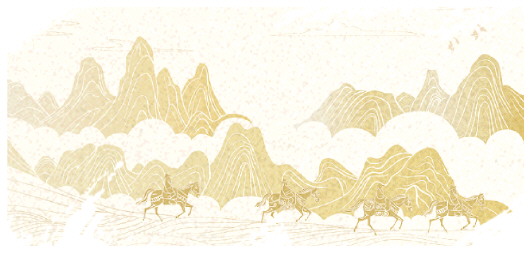05版:北海周末
05版:北海周末
- * 潍坊历史名人
- * 让词心诗意生出永恒年轮
- * 从诗词传承看活力升腾的潍坊
 08版:北海周末·悦览
08版:北海周末·悦览
- * 书香润童心
- *
在纷扰中
寻找生命的本真 - * 在路上,在远方
- * 永远的朋友
- * 全 民 阅 读 一 起 读 书
- * 剧 院 之 声
◎薛静
新疆北部生活着一群哈萨克牧民,他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保持着游牧习俗的牧民。每一年的春夏秋冬,他们都会沿着水的方向,翻过一座座山,从一个驻扎地走向下一个驻扎地。迁徙,是伴随着他们一生的命题。关于这些牧民的文字与图像,已经足够多,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为了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刻意地用文字制造出了距离感。但是到了李娟这里,距离感消失了。她笔下不仅仅有扎克拜妈妈和其他哈萨克牧民的寻常家庭生活,还有牧民们与世人共通的那部分情感,那些相同的欢乐、忧虑,以及希望。
“在吉尔阿特,哪怕站在最高的山顶上四面张望,也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个人。”《羊道 春牧场》的开篇第一句,李娟用寥寥几句,勾勒出了荒漠山坡的寂寥与空荡。为了记录下最真实的牧民迁徙过程,李娟来到扎克拜妈妈一家,成为妈妈口中的另一个女儿,与其他孩子一起赶羊、煮饭、放牛、缝衣服、做农活,一一尝尽生活的苦和甜。从最初的吉尔阿特、塔门尔图,搬迁到冬库尔、吾塞,一次比一次深入山林,一次比一次远离人群。除了《羊道 春牧场》,李娟还写下了《羊道 前山夏牧场》《羊道 深山夏牧场》。沿着季节的顺序读完三本书,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扎克拜一家走完了这半年的路。
李娟永远是坦然的,不管是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窘迫的尴尬状况,亦或是面对其他牧民好奇的打量眼光。家里的一只破旧锡盆,既装干牛粪也装新鲜面团,李娟几乎是立即就接受了这个事实。荒野里没有什么是肮脏的,火焰会抚平一切差异,无论什么最终都会变成泥土。难得一遇的拖依(聚会)上,青年男女跳舞玩闹,尽情释放着激情与活力。但李娟的注意力只在冷上,一门心思盼望着快点天亮,好回家取暖睡觉。有过路的其他牧民到家中喝茶,认出李娟是“裁缝的女儿”,即便素未相识,李娟也会惊喜地跟对方聊天。
这份坦然,或许也是所有游牧民的天性。广袤的阿勒泰山中,盛满了哈萨克族与羊群、马群、骆驼群的生活印记。他们以天地为家,遵循着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会为路上遇到的转场人家准备一碗酸奶,热心地为每一家相互传递消息,随时准备热茶招待上门的牧民,哪怕彼此间都是陌生人。转场路上,不管阴天下雨,他们都会特意换上新衣服,把一场离开与到达视为开始新生活的希望。所谓羊道,就是转场搬家时候羊走的道路,与人、骆驼并不走一条路。李娟曾经问,为什么我们不和别人一样走大路呢?家人回答说,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为了保护草场,每家人走的路线都不一样。
接受游牧生活,其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就算是哈萨克牧民也是如此。不是没有人尝试逃离这种生活,比如苏乎拉,一个极其漂亮的年轻牧羊女,也是大家眼中的叛逆者,数次试图逃离牧场,去乌鲁木齐寻找想要的现代生活。可当母亲因她的叛逆绝望死去时,苏乎拉的反抗也走到了尽头。甘愿留下来的牧民,很多因为生活艰辛、缺乏医疗资源,有着各种各样的疾病。15岁的卡西一只耳朵聋了,20岁的斯马胡力患有关节疾病,药都是一把把地吃。这些年轻人有没有向往过深山之外的现代生活?李娟没有写,我们也无法揣摩。但在一篇关于相机的文章中,李娟写道:“流行哈语歌中花哨的装饰音,年轻人服饰上夸张而无用的饰物,孩子香甜地吸吮着‘娃哈哈’,深山小道边遗落的食品包装袋……世人都需平等地进入当下世界,无论多么牢固的古旧秩序都正在被打开缺口。虽然从那个缺口进进出出的仍是传统事物,但每一出入都有些许流失和轻微的替换。”李娟感觉到了,只是李娟一个人感觉到了吗?
是啊。生活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谁都渴望追逐更轻松、更快乐的人生,谁都无法在前行的世界中独自止步。牧民与古老生产方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也许还早,也许已临近尾声。不管未来如何,且将时间停留在此刻吧。深山繁盛的夏牧场中,与家人围坐在一起,餐布展开之处绿意葳蕤,食物丰盛气氛安宁,正是一年之中最舒适、最丰饶的时光。
新疆北部生活着一群哈萨克牧民,他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还保持着游牧习俗的牧民。每一年的春夏秋冬,他们都会沿着水的方向,翻过一座座山,从一个驻扎地走向下一个驻扎地。迁徙,是伴随着他们一生的命题。关于这些牧民的文字与图像,已经足够多,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为了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刻意地用文字制造出了距离感。但是到了李娟这里,距离感消失了。她笔下不仅仅有扎克拜妈妈和其他哈萨克牧民的寻常家庭生活,还有牧民们与世人共通的那部分情感,那些相同的欢乐、忧虑,以及希望。
“在吉尔阿特,哪怕站在最高的山顶上四面张望,也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个人。”《羊道 春牧场》的开篇第一句,李娟用寥寥几句,勾勒出了荒漠山坡的寂寥与空荡。为了记录下最真实的牧民迁徙过程,李娟来到扎克拜妈妈一家,成为妈妈口中的另一个女儿,与其他孩子一起赶羊、煮饭、放牛、缝衣服、做农活,一一尝尽生活的苦和甜。从最初的吉尔阿特、塔门尔图,搬迁到冬库尔、吾塞,一次比一次深入山林,一次比一次远离人群。除了《羊道 春牧场》,李娟还写下了《羊道 前山夏牧场》《羊道 深山夏牧场》。沿着季节的顺序读完三本书,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扎克拜一家走完了这半年的路。
李娟永远是坦然的,不管是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是窘迫的尴尬状况,亦或是面对其他牧民好奇的打量眼光。家里的一只破旧锡盆,既装干牛粪也装新鲜面团,李娟几乎是立即就接受了这个事实。荒野里没有什么是肮脏的,火焰会抚平一切差异,无论什么最终都会变成泥土。难得一遇的拖依(聚会)上,青年男女跳舞玩闹,尽情释放着激情与活力。但李娟的注意力只在冷上,一门心思盼望着快点天亮,好回家取暖睡觉。有过路的其他牧民到家中喝茶,认出李娟是“裁缝的女儿”,即便素未相识,李娟也会惊喜地跟对方聊天。
这份坦然,或许也是所有游牧民的天性。广袤的阿勒泰山中,盛满了哈萨克族与羊群、马群、骆驼群的生活印记。他们以天地为家,遵循着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会为路上遇到的转场人家准备一碗酸奶,热心地为每一家相互传递消息,随时准备热茶招待上门的牧民,哪怕彼此间都是陌生人。转场路上,不管阴天下雨,他们都会特意换上新衣服,把一场离开与到达视为开始新生活的希望。所谓羊道,就是转场搬家时候羊走的道路,与人、骆驼并不走一条路。李娟曾经问,为什么我们不和别人一样走大路呢?家人回答说,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为了保护草场,每家人走的路线都不一样。
接受游牧生活,其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就算是哈萨克牧民也是如此。不是没有人尝试逃离这种生活,比如苏乎拉,一个极其漂亮的年轻牧羊女,也是大家眼中的叛逆者,数次试图逃离牧场,去乌鲁木齐寻找想要的现代生活。可当母亲因她的叛逆绝望死去时,苏乎拉的反抗也走到了尽头。甘愿留下来的牧民,很多因为生活艰辛、缺乏医疗资源,有着各种各样的疾病。15岁的卡西一只耳朵聋了,20岁的斯马胡力患有关节疾病,药都是一把把地吃。这些年轻人有没有向往过深山之外的现代生活?李娟没有写,我们也无法揣摩。但在一篇关于相机的文章中,李娟写道:“流行哈语歌中花哨的装饰音,年轻人服饰上夸张而无用的饰物,孩子香甜地吸吮着‘娃哈哈’,深山小道边遗落的食品包装袋……世人都需平等地进入当下世界,无论多么牢固的古旧秩序都正在被打开缺口。虽然从那个缺口进进出出的仍是传统事物,但每一出入都有些许流失和轻微的替换。”李娟感觉到了,只是李娟一个人感觉到了吗?
是啊。生活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谁都渴望追逐更轻松、更快乐的人生,谁都无法在前行的世界中独自止步。牧民与古老生产方式,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也许还早,也许已临近尾声。不管未来如何,且将时间停留在此刻吧。深山繁盛的夏牧场中,与家人围坐在一起,餐布展开之处绿意葳蕤,食物丰盛气氛安宁,正是一年之中最舒适、最丰饶的时光。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509/08/08-s.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