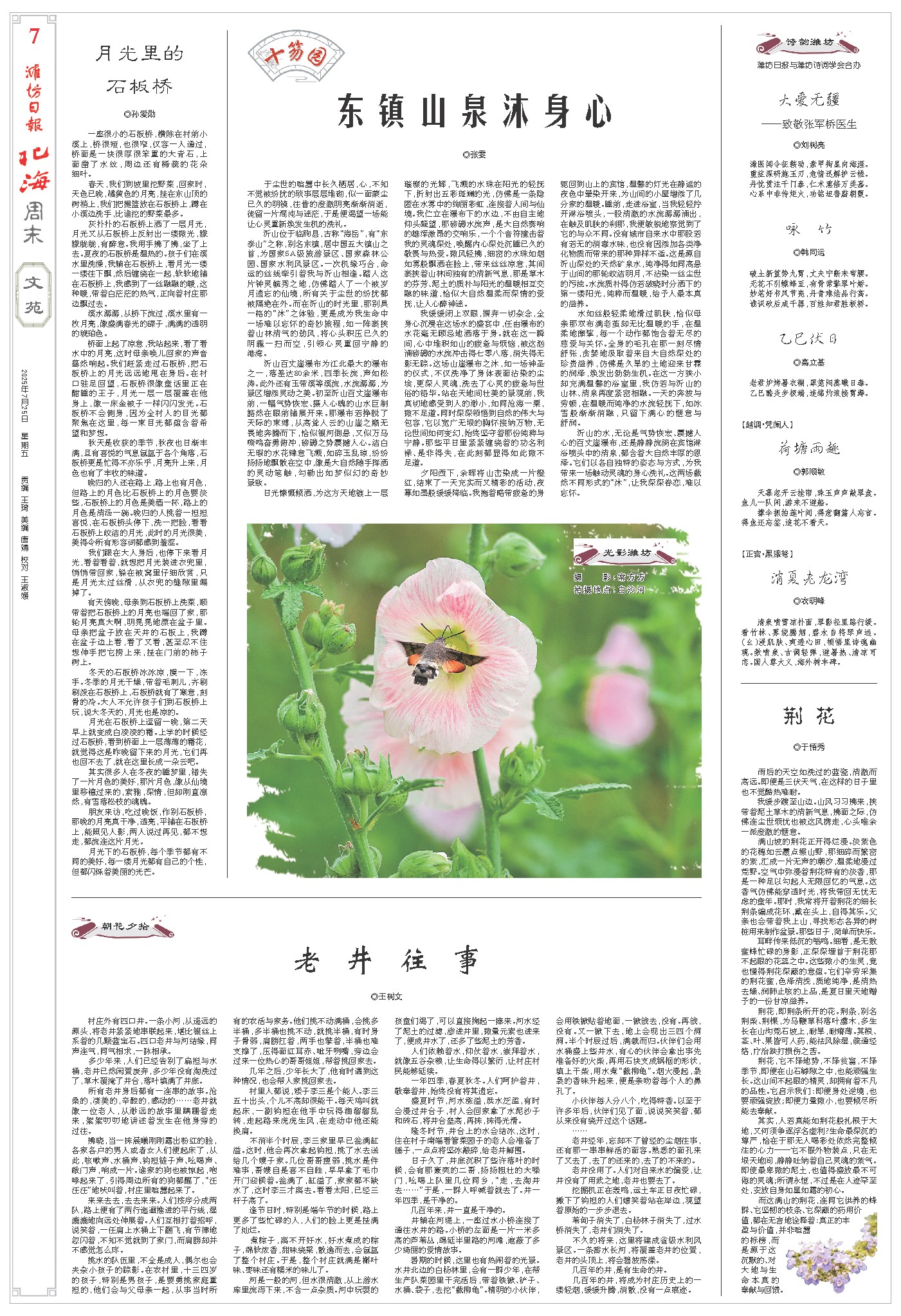◎王树文
村庄外有四口井。一条小河,从遥远的源头,将老井紧紧地串联起来,堪比银丝上系着的几颗蓝宝石。四口老井与河结缘,同声连气,同气相求,一脉相承。
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告别了扁担与水桶,老井已然闲置废弃,多少年没有淘洗过了,草木覆掩了井台,落叶填满了井底。
所有老井身后都有一连串的故事。沧桑的,凄美的,辛酸的,感动的……老井就像一位老人,从渺远的故事里蹒跚着走来,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发生在他身旁的过往。
拂晓,当一抹晨曦刚刚露出粉红的脸,各家各户的男人或者女人们便起床了,从此,咳嗽声、水桶声、钩担链子声、吆喝声、敞门声,响成一片。谁家的狗也被惊起,咆哮起来了,引得周边所有的狗都醒了,“汪汪汪”地吠叫着,村庄里喧嚣起来了。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人们按序分成两队,路上便有了两行迤逦推进的平行线,湿漉漉地向远处伸展着。人们互相打着招呼,说笑着,一任肩上水桶上下翻飞,有节律地忽闪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而肩膀却并不感觉怎么疼。
挑水的队伍里,不全是成人,偶尔也会夹杂小孩子的踪影。在农村里,十三四岁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要勇挑家庭重担的,他们会与父母亲一起,从事当时所有的农活与家务。他们挑不动满桶,会挑多半桶,多半桶也挑不动,就挑半桶,有时身子骨弱,肩膀扛着,两手也擎着,半桶也难支撑了,压得面红耳赤、呲牙咧嘴,旁边会过来一位热心的哥哥姐姐,帮着挑回家去。
几年之后,少年长大了,他有时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帮人家挑回家去。
村里人都说,矮子李三是个能人。李三五十出头,个儿不高却很能干。每天鸡叫就起床,一副钩担在他手中玩得滴溜溜乱转,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在走动中他还能换肩。
不消半个时辰,李三家里早已瓮满缸溢。这时,他会再次拿起钩担,挑了水去送给几个嫂子家。几位哥哥瘦弱,挑水是件难事,哥嫂自是喜不自胜,早早拿了毛巾开门迎候着。瓮满了,缸溢了,家家都不缺水了,这时李三才离去。看看太阳,已经三杆子高了。
逢节日时,特别是端午节的时候,路上更多了些忙碌的人,人们的脸上更是挂满了灿烂。
煮粽子,离不开好水,好水煮成的粽子,绵软浓香,甜味绕梁,散逸而去,会氤氲了整个村庄。于是,整个村庄就满是槲叶味、枣味还有糯米的味儿了。
河是一般的河,但水很清澈,从上游水库里流泻下来,不含一点杂质。河中玩耍的孩童们渴了,可以直接掬起一捧来。河水经了泥土的过滤,渗进井里,微量元素也进来了,便成井水了,还多了些泥土的芳香。
人们依赖着水,仰仗着水,崇拜着水,就像五谷杂粮,让生命得以繁衍,让村庄村民能够延续。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人们呵护着井,敬奉着井,始终没有将其遗忘。
盛夏时节,河水涨溢,洪水泛滥,有时会漫过井台子,村人会回家拿了水泥沙子和砖石,将井台垒高,再抹,抹得光滑。
隆冬时节,井台上的水会结冰,这时,住在村子南端看管菜园子的老人会准备了锤子,一点点将坚冰敲碎,给老井解围。
日子久了,井底沉积了些许落叶的时候,会有那豪爽的二哥,扬扬粗壮的大嗓门,吆喝上队里几位同乡,“走,去淘井去……”于是,一群人呼喊着就去了。井一年四季,是干净的。
几百年来,井一直是干净的。
井躺在河堤上,一座过水小桥连接了通往水井的路。小桥的左面是一片一米多高的芦苇丛,绵延半里路的河滩,遮蔽了多少绮丽的爱情故事。
暑期的时候,这里也有热闹着的光景。水井北边的白杨林里,会有一群少年,在帮生产队菜园里干完活后,带着铁锨、铲子、水桶、袋子,去挖“截柳龟”。精明的小伙伴,会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锨戗去,没有。再戗,没有。又一锨下去,地上会现出三四个洞洞。半个时辰过后,满载而归。伙伴们会用水桶盛上些井水,有心的伙伴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火柴,再用石块支成锅框的形状,填上干柴,用水煮“截柳龟”。烟火漫起,袅袅的香味升起来,便是亲吻着每个人的鼻孔了。
小伙伴每人分八个,吃得特香。以至于许多年后,伙伴们见了面,说说笑笑着,都从来没有绕开过这个话题。
……
老井经年,忘却不了曾经的尘烟往事,还有那一串串鲜活的面容。熟悉的面孔来了又去了,去了的还来的,去了的不来的。
老井没用了。人们对自来水的偏爱,让井没有了用武之地,老井也要去了。
挖掘机正在轰鸣,运土车正日夜忙碌,撇下了钩担的人们嬉笑着站在岸边,观望着原始的一步步退去。
苇甸子消失了,白杨林子消失了,过水桥消失了,老井们消失了。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成省级水利风景区。一条蓄水长河,将覆盖老井的位置,老井的头顶上,将会碧波荡漾。
几百年的井,是有生命的井。
几百年的井,将成为村庄历史上的一缕轻烟,缓缓升腾,消散,没有一点痕迹。
村庄外有四口井。一条小河,从遥远的源头,将老井紧紧地串联起来,堪比银丝上系着的几颗蓝宝石。四口老井与河结缘,同声连气,同气相求,一脉相承。
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告别了扁担与水桶,老井已然闲置废弃,多少年没有淘洗过了,草木覆掩了井台,落叶填满了井底。
所有老井身后都有一连串的故事。沧桑的,凄美的,辛酸的,感动的……老井就像一位老人,从渺远的故事里蹒跚着走来,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发生在他身旁的过往。
拂晓,当一抹晨曦刚刚露出粉红的脸,各家各户的男人或者女人们便起床了,从此,咳嗽声、水桶声、钩担链子声、吆喝声、敞门声,响成一片。谁家的狗也被惊起,咆哮起来了,引得周边所有的狗都醒了,“汪汪汪”地吠叫着,村庄里喧嚣起来了。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人们按序分成两队,路上便有了两行迤逦推进的平行线,湿漉漉地向远处伸展着。人们互相打着招呼,说笑着,一任肩上水桶上下翻飞,有节律地忽闪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而肩膀却并不感觉怎么疼。
挑水的队伍里,不全是成人,偶尔也会夹杂小孩子的踪影。在农村里,十三四岁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要勇挑家庭重担的,他们会与父母亲一起,从事当时所有的农活与家务。他们挑不动满桶,会挑多半桶,多半桶也挑不动,就挑半桶,有时身子骨弱,肩膀扛着,两手也擎着,半桶也难支撑了,压得面红耳赤、呲牙咧嘴,旁边会过来一位热心的哥哥姐姐,帮着挑回家去。
几年之后,少年长大了,他有时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帮人家挑回家去。
村里人都说,矮子李三是个能人。李三五十出头,个儿不高却很能干。每天鸡叫就起床,一副钩担在他手中玩得滴溜溜乱转,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在走动中他还能换肩。
不消半个时辰,李三家里早已瓮满缸溢。这时,他会再次拿起钩担,挑了水去送给几个嫂子家。几位哥哥瘦弱,挑水是件难事,哥嫂自是喜不自胜,早早拿了毛巾开门迎候着。瓮满了,缸溢了,家家都不缺水了,这时李三才离去。看看太阳,已经三杆子高了。
逢节日时,特别是端午节的时候,路上更多了些忙碌的人,人们的脸上更是挂满了灿烂。
煮粽子,离不开好水,好水煮成的粽子,绵软浓香,甜味绕梁,散逸而去,会氤氲了整个村庄。于是,整个村庄就满是槲叶味、枣味还有糯米的味儿了。
河是一般的河,但水很清澈,从上游水库里流泻下来,不含一点杂质。河中玩耍的孩童们渴了,可以直接掬起一捧来。河水经了泥土的过滤,渗进井里,微量元素也进来了,便成井水了,还多了些泥土的芳香。
人们依赖着水,仰仗着水,崇拜着水,就像五谷杂粮,让生命得以繁衍,让村庄村民能够延续。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人们呵护着井,敬奉着井,始终没有将其遗忘。
盛夏时节,河水涨溢,洪水泛滥,有时会漫过井台子,村人会回家拿了水泥沙子和砖石,将井台垒高,再抹,抹得光滑。
隆冬时节,井台上的水会结冰,这时,住在村子南端看管菜园子的老人会准备了锤子,一点点将坚冰敲碎,给老井解围。
日子久了,井底沉积了些许落叶的时候,会有那豪爽的二哥,扬扬粗壮的大嗓门,吆喝上队里几位同乡,“走,去淘井去……”于是,一群人呼喊着就去了。井一年四季,是干净的。
几百年来,井一直是干净的。
井躺在河堤上,一座过水小桥连接了通往水井的路。小桥的左面是一片一米多高的芦苇丛,绵延半里路的河滩,遮蔽了多少绮丽的爱情故事。
暑期的时候,这里也有热闹着的光景。水井北边的白杨林里,会有一群少年,在帮生产队菜园里干完活后,带着铁锨、铲子、水桶、袋子,去挖“截柳龟”。精明的小伙伴,会用铁锨贴着地面,一锨戗去,没有。再戗,没有。又一锨下去,地上会现出三四个洞洞。半个时辰过后,满载而归。伙伴们会用水桶盛上些井水,有心的伙伴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火柴,再用石块支成锅框的形状,填上干柴,用水煮“截柳龟”。烟火漫起,袅袅的香味升起来,便是亲吻着每个人的鼻孔了。
小伙伴每人分八个,吃得特香。以至于许多年后,伙伴们见了面,说说笑笑着,都从来没有绕开过这个话题。
……
老井经年,忘却不了曾经的尘烟往事,还有那一串串鲜活的面容。熟悉的面孔来了又去了,去了的还来的,去了的不来的。
老井没用了。人们对自来水的偏爱,让井没有了用武之地,老井也要去了。
挖掘机正在轰鸣,运土车正日夜忙碌,撇下了钩担的人们嬉笑着站在岸边,观望着原始的一步步退去。
苇甸子消失了,白杨林子消失了,过水桥消失了,老井们消失了。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成省级水利风景区。一条蓄水长河,将覆盖老井的位置,老井的头顶上,将会碧波荡漾。
几百年的井,是有生命的井。
几百年的井,将成为村庄历史上的一缕轻烟,缓缓升腾,消散,没有一点痕迹。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725/08/Page08-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