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龙刚
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村前的那片高起的阔地被整平得与村子的主体连成一片。我深刻地记着那片平地上有成片的柿子树。那是很有些树龄的柿树了,枝干粗壮,苍古嶙峋。冬天与早春,我们常常爬到树上骑在树杈上游戏玩耍。但是到了柿树发芽时,村里一位白发小脚老太就会阻止我们上树了。她担心我们会折树枝,搓掉树芽从而影响到结柿子。每见我们上树,她就喋喋不休地劝阻:“快下来吧,快下来呀,别掉下来摔着!”自此一直到柿子成熟并被摘光,她都看护着这些柿树。她家那位爷爷很懒得到柿子园来,只有到采摘柿子时他会在儿子的帮助下摘几天柿子。
柿园几乎是村里老人的消闲园。夏天在柿树下乘凉,冬日靠在柿树上晒太阳。
柿子变橙时,满树金色的诱惑。我们仰着头看那些闪耀在厚实的柿叶里的柿子,那些蜜甜诱人的果实是遥不可及的。
柿子不经过十几小时温水煮泡去涩或者熟透变软是不能吃的。随着秋天的深入,浓绿的柿树叶渐成红褐色,且开始飘落,树上的小灯笼愈发累累起来。这里偶有心急的柿子变红了,是熟透的红软柿,我们望而生津,也望而生叹,因为我无法将它摘取下来。且不说看护柿树的奶奶盯在那里,就算她不在那里,我们勉强可以爬到斜伸的粗干上,而那颗熟透的软柿却躲在一段我们刚好够不到的细枝上。看柿园的奶奶却有办法摘下它,她有一个自制的、称为“落子”的工具——一根轻巧的长竿,一端有个树杈制成的纺锤形的框,框上缝有一个小布口袋。她举着长竿,把口袋伸向软柿,软柿套进纺锤框里,一推或一拉,软柿就妥妥地落到口袋里。她收回竿子从口袋里取出柿子就分给树下玩耍的孩子。
那时的柿子真甜,甜到半生难忘。进了农历九月,各项农事也接近尾声,村里人该盘算着赶大集了。九月十三是山会,所谓的山会并不在山上,就是平素的大集,可是要比大集的规模大出许多,真有人山人海的阵势。九月的集市当然少不了应时节的柿子。集上有了柿子专区,黄灿灿的一片。父母从集上买回了柿子,我可有了短暂的大快朵颐。
我堂伯家也有几棵老柿树,柿子收获时节伯父一家将一部分柿子摘下,水煮去涩后加工成硬柿子到集上卖掉,留下一小部分焐成软柿细水长流地供家人作为零食。柿子焐好后我伯母总忘不了用一个葫芦瓢端一些送到我家。那是一年中我对柿子的最后期盼。这时的柿子树真的秃了,所有的期盼要转接到下一年了。
那时总想什么时候能痛痛快快地饱吃一顿柿子呢。物换星移,终于发现从乡村到城市,房前屋后的街巷里都栽植了许多柿树。金风起时,满树累累的橙黄的柿子在摇晃,似是向路过的人献媚般地招手,却极少有人去摘下来食用。终究是太多了,而且坊间又传说吃柿子有许多禁忌,故而多数人敬而远之。柿树已作为一种美化树,从用途上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柿子也似乎不再是一种水果了。
眼下又到初冬,我伸手摘下路边一棵红得发亮的软柿,端详了一番,忽想到空腹不能吃柿子的说法,又颇为不舍地把它放回树下了。
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村前的那片高起的阔地被整平得与村子的主体连成一片。我深刻地记着那片平地上有成片的柿子树。那是很有些树龄的柿树了,枝干粗壮,苍古嶙峋。冬天与早春,我们常常爬到树上骑在树杈上游戏玩耍。但是到了柿树发芽时,村里一位白发小脚老太就会阻止我们上树了。她担心我们会折树枝,搓掉树芽从而影响到结柿子。每见我们上树,她就喋喋不休地劝阻:“快下来吧,快下来呀,别掉下来摔着!”自此一直到柿子成熟并被摘光,她都看护着这些柿树。她家那位爷爷很懒得到柿子园来,只有到采摘柿子时他会在儿子的帮助下摘几天柿子。
柿园几乎是村里老人的消闲园。夏天在柿树下乘凉,冬日靠在柿树上晒太阳。
柿子变橙时,满树金色的诱惑。我们仰着头看那些闪耀在厚实的柿叶里的柿子,那些蜜甜诱人的果实是遥不可及的。
柿子不经过十几小时温水煮泡去涩或者熟透变软是不能吃的。随着秋天的深入,浓绿的柿树叶渐成红褐色,且开始飘落,树上的小灯笼愈发累累起来。这里偶有心急的柿子变红了,是熟透的红软柿,我们望而生津,也望而生叹,因为我无法将它摘取下来。且不说看护柿树的奶奶盯在那里,就算她不在那里,我们勉强可以爬到斜伸的粗干上,而那颗熟透的软柿却躲在一段我们刚好够不到的细枝上。看柿园的奶奶却有办法摘下它,她有一个自制的、称为“落子”的工具——一根轻巧的长竿,一端有个树杈制成的纺锤形的框,框上缝有一个小布口袋。她举着长竿,把口袋伸向软柿,软柿套进纺锤框里,一推或一拉,软柿就妥妥地落到口袋里。她收回竿子从口袋里取出柿子就分给树下玩耍的孩子。
那时的柿子真甜,甜到半生难忘。进了农历九月,各项农事也接近尾声,村里人该盘算着赶大集了。九月十三是山会,所谓的山会并不在山上,就是平素的大集,可是要比大集的规模大出许多,真有人山人海的阵势。九月的集市当然少不了应时节的柿子。集上有了柿子专区,黄灿灿的一片。父母从集上买回了柿子,我可有了短暂的大快朵颐。
我堂伯家也有几棵老柿树,柿子收获时节伯父一家将一部分柿子摘下,水煮去涩后加工成硬柿子到集上卖掉,留下一小部分焐成软柿细水长流地供家人作为零食。柿子焐好后我伯母总忘不了用一个葫芦瓢端一些送到我家。那是一年中我对柿子的最后期盼。这时的柿子树真的秃了,所有的期盼要转接到下一年了。
那时总想什么时候能痛痛快快地饱吃一顿柿子呢。物换星移,终于发现从乡村到城市,房前屋后的街巷里都栽植了许多柿树。金风起时,满树累累的橙黄的柿子在摇晃,似是向路过的人献媚般地招手,却极少有人去摘下来食用。终究是太多了,而且坊间又传说吃柿子有许多禁忌,故而多数人敬而远之。柿树已作为一种美化树,从用途上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柿子也似乎不再是一种水果了。
眼下又到初冬,我伸手摘下路边一棵红得发亮的软柿,端详了一番,忽想到空腹不能吃柿子的说法,又颇为不舍地把它放回树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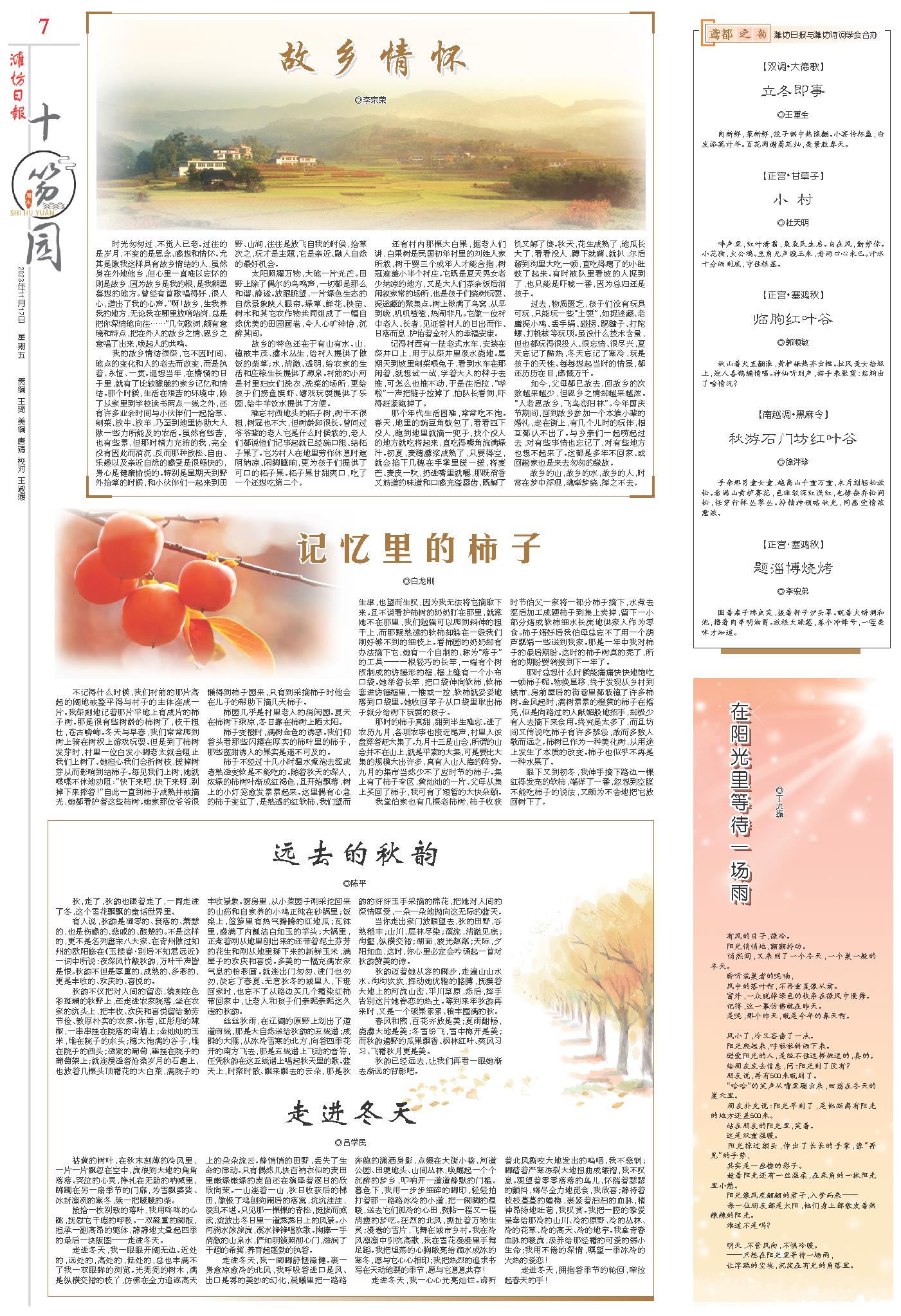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1117/08/Page08-15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