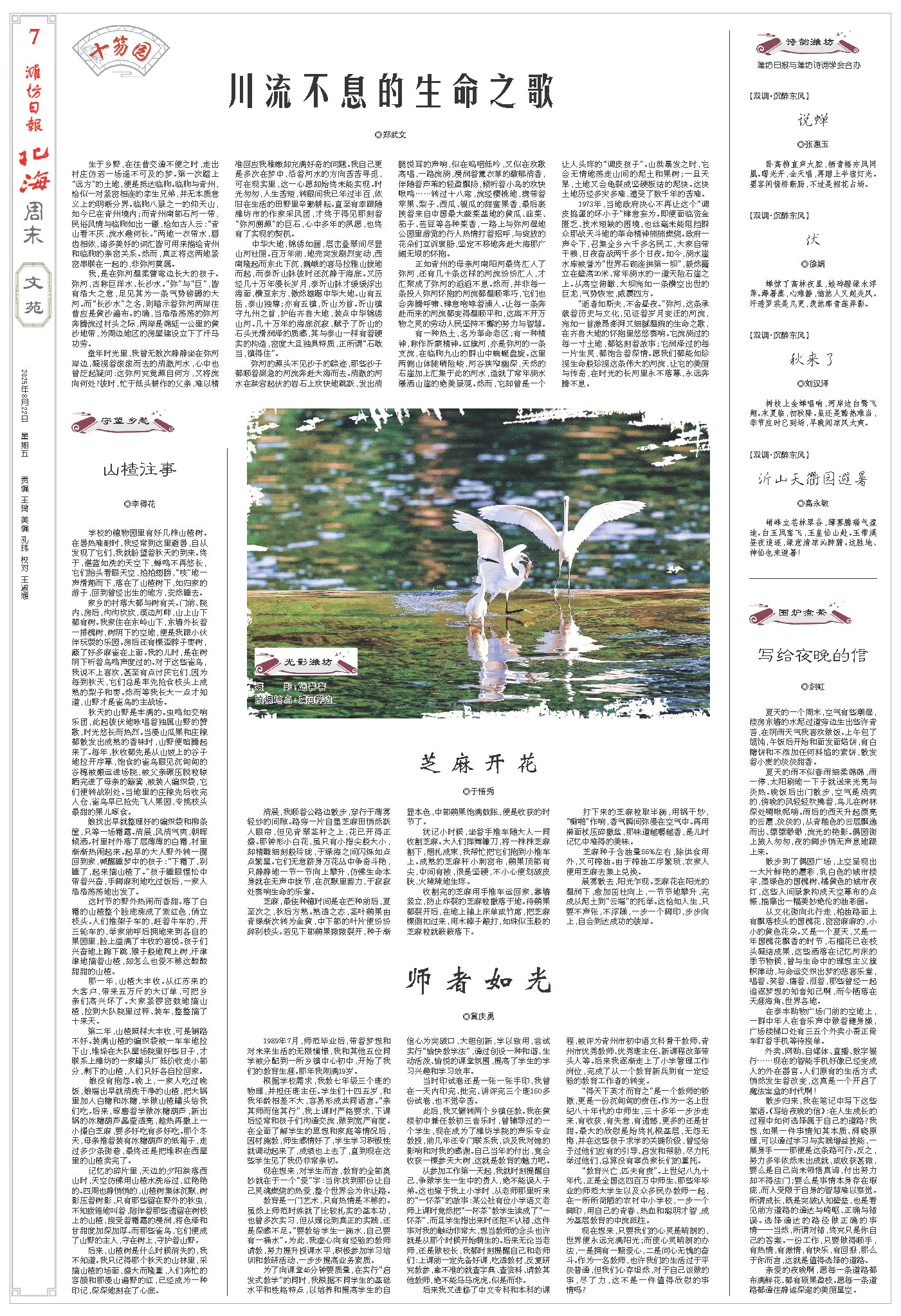08版:北海周末·悦览
08版:北海周末·悦览
- * 儿童成长的助跑器
- * 烽火家书抵万金
- * 无名之辈亦可活出自身价值
- * 一 起 读 书
- * 剧院之声
◎李得花
学校的植物园里有好几株山楂树。在暑热难耐时,我经常到这里避暑,自从发现了它们,我就盼望着秋天的到来。终于,湛蓝如洗的天空下,蝉鸣不再悠长,它们抬头看眼天空,拍拍翅膀,“吱”地一声滑翔而下,落在了山楂树下,如归家的游子,回到曾经出生的地方,安然睡去。
家乡的村落大都与树有关。门前、院内、房后,沟沟坎坎,溪边河畔,山上山下都有树。我家住在东岭山下,东墙外长着一排槐树,树阴下的空地,便是我跟小伙伴玩耍的乐园。房后还有棵歪脖子枣树,藏了好多麻雀在上面。我的儿时,是在树阴下听着鸟鸣声度过的。对于这些雀鸟,我说不上喜欢,甚至有点讨厌它们,因为每到秋天,它们总是率先抢食枝头上成熟的梨子和枣。然而等我长大一点才知道,山野才是雀鸟的主战场。
秋天的山野是丰满的。虫鸣如交响乐团,此起彼伏地咏唱着独属山野的赞歌,时光悠长而热烈。当漫山瓜果和庄稼都散发出成熟的香味时,山野便喧腾起来了。每年,秋收都先是从山坡上的谷子地拉开序幕,饱食的雀鸟眼见沉甸甸的谷穗被搬运进场院,被父亲碾压脱粒晾晒完进了母亲的簸箕,被装入编织袋,它们便转战别处。当地里的庄稼先后收完入仓,雀鸟早已抢先飞入果园,专挑枝头最甜的果儿啄食。
娘找出早就整理好的编织袋和柳条筐,只等一场霜露。清晨,风清气爽,朝晖倾洒。村里村外落了层薄薄的白霜,村里渐渐热闹起来。起早的大人野外转一圈回到家,喊醒睡梦中的孩子:“下霜了,别睡了,起来摘山楂了。”孩子睡眼惺忪中带着兴奋,手脚麻利地吃过饭后,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这时节的野外热闹而香甜。落了白霜的山楂整个脸庞涨成了紫红色,俏立枝头。人们推架子车的,赶着牛车的,开三轮车的,举家前呼后拥地来到各自的果园里,脸上溢满了丰收的喜悦。孩子们兴奋地上蹿下跳,猴子般地爬上树,汗津津地摘着山楂,却怎么也爱不够这酸酸甜甜的山楂。
那一年,山楂大丰收。从江苏来的大客户,带来五万斤的大订单,可把乡亲们高兴坏了。大家紧锣密鼓地摘山楂,拉到大队院里过秤、装车,整整摘了十来天。
第二年,山楂照样大丰收,可是销路不好。装满山楂的编织袋被一车车地拉下山,堆垛在大队屋场院里好些日子,才联系上潍坊的一家罐头厂低价收走小部分,剩下的山楂,人们只好各自拉回家。
娘没有抱怨。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娘端出早就清洗干净的山楂,把大锅里加入白糖和冰糖,学做山楂罐头给我们吃。后来,琢磨着学做冰糖葫芦,新出锅的冰糖葫芦晶莹透亮,趁热再撒上一小撮白芝麻,要多好吃有多好吃。那个冬天,母亲推着装有冰糖葫芦的纸箱子,走过多少条街巷,最终还是把堆积在西屋里的山楂卖完了。
记忆的碎片里,天边的夕阳跌落西山时,天空仿佛用山楂水洗浴过,红艳艳的。四周也静悄悄的,山楂树集体沉默,树影压着树影,只有那些留在野外的秋虫,不知疲倦地叫着,陪伴着那些遗留在树枝上的山楂,接受着霜露的浸润,将色泽和甘甜度加深加厚。而那些雀鸟,它们便成了山野的主人,守在树上,守护着山野。
后来,山楂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个秋天的山林里,采摘山楂的场面,盛大而隆重,人们奔忙的容颜和那漫山遍野的红,已经成为一种印记,深深地刻在了心底。
学校的植物园里有好几株山楂树。在暑热难耐时,我经常到这里避暑,自从发现了它们,我就盼望着秋天的到来。终于,湛蓝如洗的天空下,蝉鸣不再悠长,它们抬头看眼天空,拍拍翅膀,“吱”地一声滑翔而下,落在了山楂树下,如归家的游子,回到曾经出生的地方,安然睡去。
家乡的村落大都与树有关。门前、院内、房后,沟沟坎坎,溪边河畔,山上山下都有树。我家住在东岭山下,东墙外长着一排槐树,树阴下的空地,便是我跟小伙伴玩耍的乐园。房后还有棵歪脖子枣树,藏了好多麻雀在上面。我的儿时,是在树阴下听着鸟鸣声度过的。对于这些雀鸟,我说不上喜欢,甚至有点讨厌它们,因为每到秋天,它们总是率先抢食枝头上成熟的梨子和枣。然而等我长大一点才知道,山野才是雀鸟的主战场。
秋天的山野是丰满的。虫鸣如交响乐团,此起彼伏地咏唱着独属山野的赞歌,时光悠长而热烈。当漫山瓜果和庄稼都散发出成熟的香味时,山野便喧腾起来了。每年,秋收都先是从山坡上的谷子地拉开序幕,饱食的雀鸟眼见沉甸甸的谷穗被搬运进场院,被父亲碾压脱粒晾晒完进了母亲的簸箕,被装入编织袋,它们便转战别处。当地里的庄稼先后收完入仓,雀鸟早已抢先飞入果园,专挑枝头最甜的果儿啄食。
娘找出早就整理好的编织袋和柳条筐,只等一场霜露。清晨,风清气爽,朝晖倾洒。村里村外落了层薄薄的白霜,村里渐渐热闹起来。起早的大人野外转一圈回到家,喊醒睡梦中的孩子:“下霜了,别睡了,起来摘山楂了。”孩子睡眼惺忪中带着兴奋,手脚麻利地吃过饭后,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这时节的野外热闹而香甜。落了白霜的山楂整个脸庞涨成了紫红色,俏立枝头。人们推架子车的,赶着牛车的,开三轮车的,举家前呼后拥地来到各自的果园里,脸上溢满了丰收的喜悦。孩子们兴奋地上蹿下跳,猴子般地爬上树,汗津津地摘着山楂,却怎么也爱不够这酸酸甜甜的山楂。
那一年,山楂大丰收。从江苏来的大客户,带来五万斤的大订单,可把乡亲们高兴坏了。大家紧锣密鼓地摘山楂,拉到大队院里过秤、装车,整整摘了十来天。
第二年,山楂照样大丰收,可是销路不好。装满山楂的编织袋被一车车地拉下山,堆垛在大队屋场院里好些日子,才联系上潍坊的一家罐头厂低价收走小部分,剩下的山楂,人们只好各自拉回家。
娘没有抱怨。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娘端出早就清洗干净的山楂,把大锅里加入白糖和冰糖,学做山楂罐头给我们吃。后来,琢磨着学做冰糖葫芦,新出锅的冰糖葫芦晶莹透亮,趁热再撒上一小撮白芝麻,要多好吃有多好吃。那个冬天,母亲推着装有冰糖葫芦的纸箱子,走过多少条街巷,最终还是把堆积在西屋里的山楂卖完了。
记忆的碎片里,天边的夕阳跌落西山时,天空仿佛用山楂水洗浴过,红艳艳的。四周也静悄悄的,山楂树集体沉默,树影压着树影,只有那些留在野外的秋虫,不知疲倦地叫着,陪伴着那些遗留在树枝上的山楂,接受着霜露的浸润,将色泽和甘甜度加深加厚。而那些雀鸟,它们便成了山野的主人,守在树上,守护着山野。
后来,山楂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个秋天的山林里,采摘山楂的场面,盛大而隆重,人们奔忙的容颜和那漫山遍野的红,已经成为一种印记,深深地刻在了心底。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7/07-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0822/08/Page08-15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