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璇
端午节本称为“端五”,海岱方言则称“五月单五”。所谓“单五”,是相对于十五、二十五而言。“端”者,开端也,即“开头”之意。五月之中有三个“五日”,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五自是“头五”,十五自是“中五”,二十五则是“末五”。“头五”即是端五,后演化为“端午”。
端午节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以下几个说法:
纪念屈原说
屈原,名平,战国时期楚国人,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群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大臣靳尚嫉贤妒能,进谗诬陷,以致楚怀王怒而疏之。屈原失宠,遂作《离骚》。离骚者,离忧也。
后来屈原受贬遭迁,至于江滨,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史记·屈原传》中只字未提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只有后人出版的《史记》附录注文时,才把南朝梁国吴均的《续齐谐记》中有关屈原的记载附录其后:“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续齐谐记》是谐记类作品,类似于趣闻野说般小道消息之属,难免人为猎奇成分。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附录《襄阳风俗记》文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显然,这也是传说之类,难以相信。不过现实生活中端午节祭屈原说还是较普遍。
纪念伍子胥说
伍子胥谏吴伐齐,主张彻底灭越国。而越王施离间计,买通吴国奸臣伯嚭在吴王面前进献谗言,以致伍子胥以言获罪,被赐剑自裁。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而死。
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
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山。从《史记·伍子胥传》中来看,子胥之死并未与端午节相联系,后人所说的龙舟竞渡乃是纪念伍子胥亦是毫无根据。
纪念曹娥说
曹娥者,曹姓之美女也,浙江会稽上虞人,生于东汉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投江而死,以孝女闻名于时。《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曹娥传》,据其记载,曹娥的父亲曹盱在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溺死,曹娥沿江号哭寻父未得,昼夜不停,连哭了十七天而投江寻父,后竟背着其父尸体浮出水面,时人称之曰孝,为其立庙,曰:曹娥庙。一个十四岁女孩竟以孝闻名于时,从此,此江更名曰:曹娥江。
东汉文学家邯郸淳撰文称颂,并刻成《曹娥碑》。
大文学家蔡邕经过曹娥碑,因天黑难辨,只好摸着刻石铭文,阅读了全文,感喟不已,遂于碑阴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大字。由于蔡邕还是知名的书法家,所以其题字被人刻在了石碑上。不过八个字是一则谜语,一般人莫名其妙。
三国时魏国主簿杨修才思敏捷,竟能解开谜底:黄绢,色丝也。色、丝相合乃是“绝”字;幼妇即是少女,女、少相合乃是“妙”字;外孙,女儿之子也,女、子相合乃是“好”字;齑臼,乃受五辛之器,受、辛相合乃是“辤”字。四字相连乃是“绝妙好辞”。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捷悟》和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均涉及了曹娥碑,可见曹娥果有其人。但说端午节缘于纪念曹娥之说并无确切根据。除此之外,还有越王勾践操练水兵之说。其实上述种种传说都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当地有名有趣的事件拿到外地去未必有影响,根据诸多文献资料判断:端午节的来历,楚人以为是源于屈原,越人以为是源于勾践,吴人以为源于伍子胥,都是根据各自传说附会诠释。
古人的“卫生防疫日”
端五节,确指农历五月初五,俗以为五月是“恶月”“毒月”,而五月中的五日,是毒上之毒,称“五毒之日”。民间所说的“五毒”指毒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时值五月,五毒繁殖最为兴旺,俗以为五月之“五毒”毒性最大。
古代医学落后,不隔几年便瘟疫流行,一旦出现瘟疫,村人相互传染,常常是百不存一,只有极少数逃匿人迹罕至偏僻处者,方能躲过此劫。古人深知瘟疫是通过空气传播,他们认为传播瘟疫的“恶气”是致命之毒,每至五月五日,妇女儿童都要佩戴香囊,以止“恶气”。
香囊,俗名“香布袋”,内盛朱砂、雄黄、艾叶、藿香、苍术等物,用红绳挂于颈项,垂于胸前,古人认为香囊之气能杀灭恶气之毒。作为家庭,端午节早晨便门插艾蒿、菖蒲,甚至桃枝,意在辟邪性止恶气。古人认为:要用“菖蒲作剑,悬以辟邪”,用艾蒿、菖蒲止“五毒”恶气入宅。
《本草纲目》记载:“菖蒲气温味辛,功能解毒杀虫。艾叶气芳香,能通九窍,灸疾病。”现在每逢端午节,北方民俗是插艾蒿,俗谓薰“五毒”。《荆楚岁时记》曰:“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同时民俗喜以艾蒿扎制成虎形,又用菖蒲扎成龙形,名曰:艾虎,蒲龙。《荆楚岁时记》曰:“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取戴之。”而《燕京岁时记》曰:“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
古之端午节尚有饮菖蒲酒的习俗,目的是祛瘟止毒。唐代以后人们开始饮雄黄酒。雄黄是含有硫化砷的结晶体,浸酒之后有害健康,会引起慢性砷中毒,但雄黄酒外用则有驱瘟除毒之功效。
为了辟邪,秦汉时期人们还使用了桃印。汉朝之桃印长六寸、宽三寸,以五色书符文,悬门上。《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朱索,五色(缕)、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
古人把五月五日视为“五毒日”,有除“五毒”之举,房内贴“五毒图”。所谓“五毒图”,实为红纸上绘印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以针刺扎于其身,认为此举可以遏制“五毒”兴作。
总之,在古代,端午节也是“卫生防疫日”。古人应对瘟疫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具有普遍性,后来演化成风俗,这一点也是由诸多文献记载印证出来的。
端午节本称为“端五”,海岱方言则称“五月单五”。所谓“单五”,是相对于十五、二十五而言。“端”者,开端也,即“开头”之意。五月之中有三个“五日”,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五自是“头五”,十五自是“中五”,二十五则是“末五”。“头五”即是端五,后演化为“端午”。
端午节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以下几个说法:
纪念屈原说
屈原,名平,战国时期楚国人,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群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大臣靳尚嫉贤妒能,进谗诬陷,以致楚怀王怒而疏之。屈原失宠,遂作《离骚》。离骚者,离忧也。
后来屈原受贬遭迁,至于江滨,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史记·屈原传》中只字未提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只有后人出版的《史记》附录注文时,才把南朝梁国吴均的《续齐谐记》中有关屈原的记载附录其后:“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续齐谐记》是谐记类作品,类似于趣闻野说般小道消息之属,难免人为猎奇成分。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附录《襄阳风俗记》文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显然,这也是传说之类,难以相信。不过现实生活中端午节祭屈原说还是较普遍。
纪念伍子胥说
伍子胥谏吴伐齐,主张彻底灭越国。而越王施离间计,买通吴国奸臣伯嚭在吴王面前进献谗言,以致伍子胥以言获罪,被赐剑自裁。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而死。
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
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山。从《史记·伍子胥传》中来看,子胥之死并未与端午节相联系,后人所说的龙舟竞渡乃是纪念伍子胥亦是毫无根据。
纪念曹娥说
曹娥者,曹姓之美女也,浙江会稽上虞人,生于东汉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投江而死,以孝女闻名于时。《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曹娥传》,据其记载,曹娥的父亲曹盱在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溺死,曹娥沿江号哭寻父未得,昼夜不停,连哭了十七天而投江寻父,后竟背着其父尸体浮出水面,时人称之曰孝,为其立庙,曰:曹娥庙。一个十四岁女孩竟以孝闻名于时,从此,此江更名曰:曹娥江。
东汉文学家邯郸淳撰文称颂,并刻成《曹娥碑》。
大文学家蔡邕经过曹娥碑,因天黑难辨,只好摸着刻石铭文,阅读了全文,感喟不已,遂于碑阴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大字。由于蔡邕还是知名的书法家,所以其题字被人刻在了石碑上。不过八个字是一则谜语,一般人莫名其妙。
三国时魏国主簿杨修才思敏捷,竟能解开谜底:黄绢,色丝也。色、丝相合乃是“绝”字;幼妇即是少女,女、少相合乃是“妙”字;外孙,女儿之子也,女、子相合乃是“好”字;齑臼,乃受五辛之器,受、辛相合乃是“辤”字。四字相连乃是“绝妙好辞”。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捷悟》和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均涉及了曹娥碑,可见曹娥果有其人。但说端午节缘于纪念曹娥之说并无确切根据。除此之外,还有越王勾践操练水兵之说。其实上述种种传说都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当地有名有趣的事件拿到外地去未必有影响,根据诸多文献资料判断:端午节的来历,楚人以为是源于屈原,越人以为是源于勾践,吴人以为源于伍子胥,都是根据各自传说附会诠释。
古人的“卫生防疫日”
端五节,确指农历五月初五,俗以为五月是“恶月”“毒月”,而五月中的五日,是毒上之毒,称“五毒之日”。民间所说的“五毒”指毒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时值五月,五毒繁殖最为兴旺,俗以为五月之“五毒”毒性最大。
古代医学落后,不隔几年便瘟疫流行,一旦出现瘟疫,村人相互传染,常常是百不存一,只有极少数逃匿人迹罕至偏僻处者,方能躲过此劫。古人深知瘟疫是通过空气传播,他们认为传播瘟疫的“恶气”是致命之毒,每至五月五日,妇女儿童都要佩戴香囊,以止“恶气”。
香囊,俗名“香布袋”,内盛朱砂、雄黄、艾叶、藿香、苍术等物,用红绳挂于颈项,垂于胸前,古人认为香囊之气能杀灭恶气之毒。作为家庭,端午节早晨便门插艾蒿、菖蒲,甚至桃枝,意在辟邪性止恶气。古人认为:要用“菖蒲作剑,悬以辟邪”,用艾蒿、菖蒲止“五毒”恶气入宅。
《本草纲目》记载:“菖蒲气温味辛,功能解毒杀虫。艾叶气芳香,能通九窍,灸疾病。”现在每逢端午节,北方民俗是插艾蒿,俗谓薰“五毒”。《荆楚岁时记》曰:“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同时民俗喜以艾蒿扎制成虎形,又用菖蒲扎成龙形,名曰:艾虎,蒲龙。《荆楚岁时记》曰:“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取戴之。”而《燕京岁时记》曰:“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
古之端午节尚有饮菖蒲酒的习俗,目的是祛瘟止毒。唐代以后人们开始饮雄黄酒。雄黄是含有硫化砷的结晶体,浸酒之后有害健康,会引起慢性砷中毒,但雄黄酒外用则有驱瘟除毒之功效。
为了辟邪,秦汉时期人们还使用了桃印。汉朝之桃印长六寸、宽三寸,以五色书符文,悬门上。《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朱索,五色(缕)、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
古人把五月五日视为“五毒日”,有除“五毒”之举,房内贴“五毒图”。所谓“五毒图”,实为红纸上绘印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以针刺扎于其身,认为此举可以遏制“五毒”兴作。
总之,在古代,端午节也是“卫生防疫日”。古人应对瘟疫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具有普遍性,后来演化成风俗,这一点也是由诸多文献记载印证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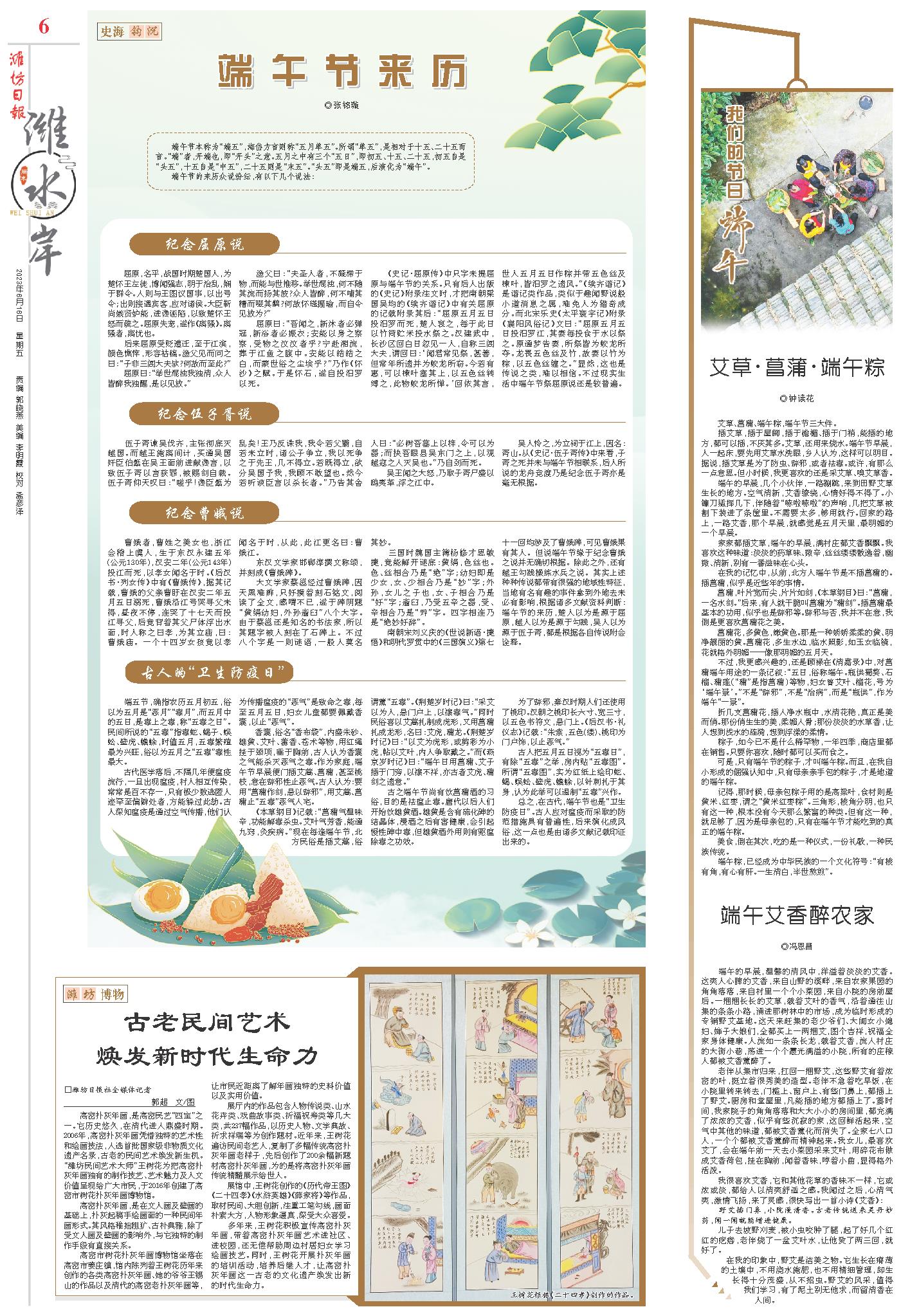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7/Page07-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30616/08/Page08-150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