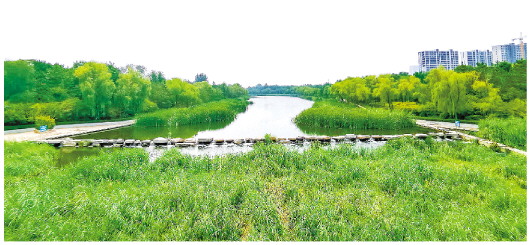05版:北海周末
05版:北海周末
- * 唐赛儿
- * 潍水潮起处 非遗正青春
- * 让非遗焕发青春光彩
 06版:北海周末·风物
06版:北海周末·风物
- * 漫话寒亭“街里”
- *
中国传拓技艺的
传承和价值 - * 与汉代的时尚相逢
 08版:北海周末·悦览
08版:北海周末·悦览
- * 雨窗书韵
- * 一幕宏大的诗宴历史剧
- * 在时光里捡拾散落的诗意
- * 一 起 读 书
- * 剧院之声
◎刘志伟
家中长辈闲谈时,常提起我家曾在寒亭“街里”落脚。这个带着乡土温度的称谓,在我心底悄然生根。近日特意邀几位长者围坐,又翻阅故纸残卷,那些沉睡的旧日轶事,便随着袅袅茶香,渐渐苏醒。
据考,寒亭村旧时多为民居,环村有一道圩子墙,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东、西两座主门之上,各矗立一间阁楼。连通东西门的村中道路,便是百姓口中的“寒亭街”,而“街里”这一称呼,也由此而来。
这片与县城隔河相望的土地,名义上虽为村庄,却藏着比县城更悠远的光阴。
夏代寒国在此立基,至王莽篡政“凡古国皆立亭”而定名“寒亭”,寒浞、嫦娥的传说在此流传数千年。数千年的积淀,早已使它成为这片土地隐秘的心脏,经济与文化的血脉,皆在此缠绕生长。
浞河水依旧北流,河东那片曾名“街里”的土地,往昔繁华仍是两岸最鲜活的印记:气派的完小里,书声穿透晨雾;木构戏园中,锣鼓震得窗棂微颤;钟表店的橱窗映着行人,书店的油墨香与药铺的草木气在巷间交织。就连河西县城未有的压水井,在此也能汩汩涌出清泉,那水声里,满是“街里”人藏不住的骄傲。即便后来县府西迁,在许多人心中,河西仍是“乡下”,唯有“街里”,才配称“热闹”。
老街是“街里”的筋骨。一条千米主街横贯东西,串起数条藏有七道弯的深巷,引孩童迈步探寻未知。西口圩墙已逝,唯留砂灰门基,门外伯明桥依旧跨河而立。桥名取自寒国古君伯明氏,河名源自夏代寒浞,二者早已将传奇刻入土地的肌理。立于桥头远望,于家大院的青砖灰瓦在民居中格外醒目。如今大院已成旧物展馆,连当年为于家守孝特制的“孝灶王”年画,以及画后的故事,都成了展陈之外的悠长余韵。
戏园子是“街里”的文化心脏。那时河西大礼堂放电影,河东戏园唱大戏,两张海报并肩于街口,如一场无声的较量。
高庙是“街里”的制高点。十米土台,曾是方圆百里的“屋脊”。南北朝时所建庙宇虽已不存,土台仍是孩童的乐园。立于台顶远眺,民房屋瓦层叠,槐桐枝梢穿插檐间,恍然让人读懂书中描写的景致。如今台上重建庙宇,恢复“云台山”旧名。清代阮元曾过此,留下“海右无如此间古,斟鄩亭北有寒亭”之句,仿佛仍在台畔回响,只是能听见的人,日渐稀少。
往昔,连接县城的大石桥西端右转,便通县城后街;而县城主街前街却是死胡同,至河西村即止。上世纪70年代初,前街新建一座通往“街里”的水泥大桥,却鲜有人行——或因它接通的是“街里”并不热闹的前街。为开通此路,规模不小的寒亭完小被整体拆除。那时流传一句顺口溜:“一个县城四盏灯,一个警察管全城;电话不如跑得快,建个大桥闲起来。”后大石桥拆,后街断行;水泥桥渐有人迹,而“街里”却自此式微。
如今的“街里”,真的只是一个村庄了。虽然随时代发展已成为县城一部分,却也不得不承认,它渐渐成了人们口中的“城中村”。“街里”之称在年轻人耳中早已陌生,更少人知这里曾是古寒国都城,是阮元笔下“海右无如此间古”之地。
如今浞河两岸建起景观带,伯明桥旧址立起新木桥,却少人驻足。老街不再,青砖房被新式民宅取代,偶有标牌保护的老屋,也难寻当年风光。
浞河水静静北去,带走了“街里”的喧闹,却带不走时光镌刻的印记。伯明桥的旧石、戏园的老木、高庙的土粒,还有那句久违的“街里”,仍在一代人记忆深处沉眠,等待某个熟悉的瞬间被唤醒。只是不知,那座崭新的木桥,是否也会有被遗忘的一日,如同曾经鲜活的“街里”,在时代的浪潮中,渐渐退为历史的背影。
唯愿光阴善待这片土地,让故地在变迁中寻得新生,越来越好。
家中长辈闲谈时,常提起我家曾在寒亭“街里”落脚。这个带着乡土温度的称谓,在我心底悄然生根。近日特意邀几位长者围坐,又翻阅故纸残卷,那些沉睡的旧日轶事,便随着袅袅茶香,渐渐苏醒。
据考,寒亭村旧时多为民居,环村有一道圩子墙,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东、西两座主门之上,各矗立一间阁楼。连通东西门的村中道路,便是百姓口中的“寒亭街”,而“街里”这一称呼,也由此而来。
这片与县城隔河相望的土地,名义上虽为村庄,却藏着比县城更悠远的光阴。
夏代寒国在此立基,至王莽篡政“凡古国皆立亭”而定名“寒亭”,寒浞、嫦娥的传说在此流传数千年。数千年的积淀,早已使它成为这片土地隐秘的心脏,经济与文化的血脉,皆在此缠绕生长。
浞河水依旧北流,河东那片曾名“街里”的土地,往昔繁华仍是两岸最鲜活的印记:气派的完小里,书声穿透晨雾;木构戏园中,锣鼓震得窗棂微颤;钟表店的橱窗映着行人,书店的油墨香与药铺的草木气在巷间交织。就连河西县城未有的压水井,在此也能汩汩涌出清泉,那水声里,满是“街里”人藏不住的骄傲。即便后来县府西迁,在许多人心中,河西仍是“乡下”,唯有“街里”,才配称“热闹”。
老街是“街里”的筋骨。一条千米主街横贯东西,串起数条藏有七道弯的深巷,引孩童迈步探寻未知。西口圩墙已逝,唯留砂灰门基,门外伯明桥依旧跨河而立。桥名取自寒国古君伯明氏,河名源自夏代寒浞,二者早已将传奇刻入土地的肌理。立于桥头远望,于家大院的青砖灰瓦在民居中格外醒目。如今大院已成旧物展馆,连当年为于家守孝特制的“孝灶王”年画,以及画后的故事,都成了展陈之外的悠长余韵。
戏园子是“街里”的文化心脏。那时河西大礼堂放电影,河东戏园唱大戏,两张海报并肩于街口,如一场无声的较量。
高庙是“街里”的制高点。十米土台,曾是方圆百里的“屋脊”。南北朝时所建庙宇虽已不存,土台仍是孩童的乐园。立于台顶远眺,民房屋瓦层叠,槐桐枝梢穿插檐间,恍然让人读懂书中描写的景致。如今台上重建庙宇,恢复“云台山”旧名。清代阮元曾过此,留下“海右无如此间古,斟鄩亭北有寒亭”之句,仿佛仍在台畔回响,只是能听见的人,日渐稀少。
往昔,连接县城的大石桥西端右转,便通县城后街;而县城主街前街却是死胡同,至河西村即止。上世纪70年代初,前街新建一座通往“街里”的水泥大桥,却鲜有人行——或因它接通的是“街里”并不热闹的前街。为开通此路,规模不小的寒亭完小被整体拆除。那时流传一句顺口溜:“一个县城四盏灯,一个警察管全城;电话不如跑得快,建个大桥闲起来。”后大石桥拆,后街断行;水泥桥渐有人迹,而“街里”却自此式微。
如今的“街里”,真的只是一个村庄了。虽然随时代发展已成为县城一部分,却也不得不承认,它渐渐成了人们口中的“城中村”。“街里”之称在年轻人耳中早已陌生,更少人知这里曾是古寒国都城,是阮元笔下“海右无如此间古”之地。
如今浞河两岸建起景观带,伯明桥旧址立起新木桥,却少人驻足。老街不再,青砖房被新式民宅取代,偶有标牌保护的老屋,也难寻当年风光。
浞河水静静北去,带走了“街里”的喧闹,却带不走时光镌刻的印记。伯明桥的旧石、戏园的老木、高庙的土粒,还有那句久违的“街里”,仍在一代人记忆深处沉眠,等待某个熟悉的瞬间被唤醒。只是不知,那座崭新的木桥,是否也会有被遗忘的一日,如同曾经鲜活的“街里”,在时代的浪潮中,渐渐退为历史的背影。
唯愿光阴善待这片土地,让故地在变迁中寻得新生,越来越好。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1/01-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2/02-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3/03-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4/04-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5/05-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6/06-s.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7/Page07-1500.jpg)
![****处理标记:[page]时, 字段 []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 ****](../../IMAGE/20251031/08/Page08-1500.jpg)